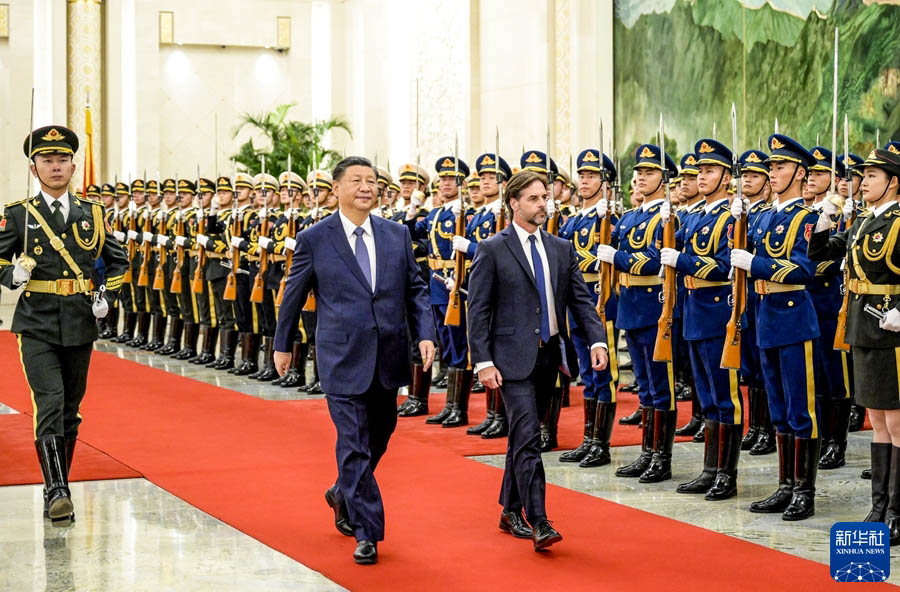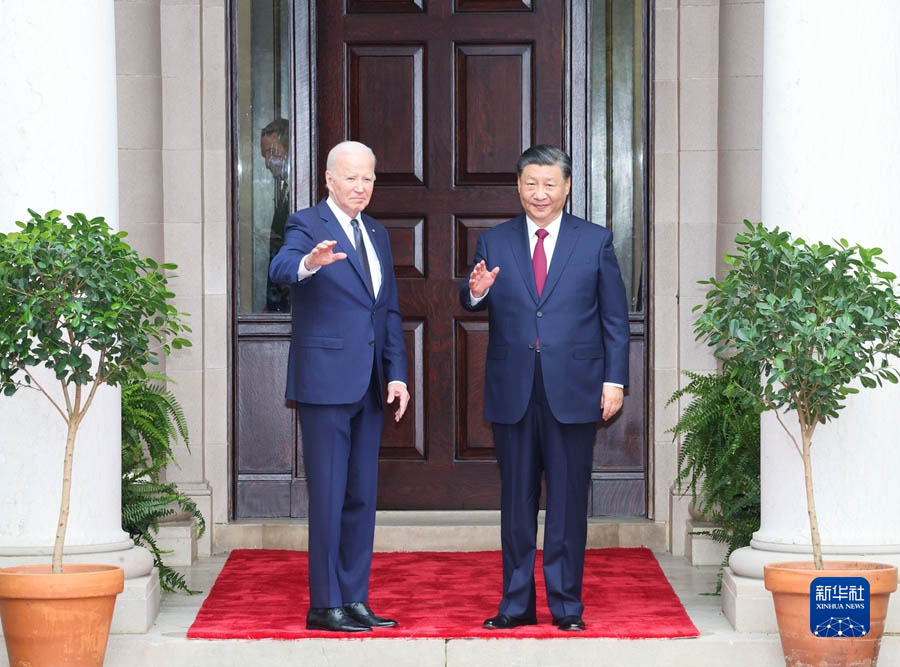古陶 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缩影
2014-03-15 17:21 来源:西藏新闻网 点击:0
考古证实,我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分布遍及全国各地,其分布主要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北方地区等五个大区域,其中西南地区就包括西藏、四川、贵州和云南。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西藏古陶器文化也得到了较长足的发展,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
西藏目前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昌都的卡若遗址、小恩达和江钦遗址,拉萨的曲贡遗址,山南的昌果沟和邦嘎遗址等,其中卡若遗址是西藏至今发现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西藏博物馆陶器陈列中居多的是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出土的,其次是贡嘎昌果沟等遗址出土的。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无论从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具规模,其器形、装饰、纹样等具有高原早期制陶工艺技术的典型特征。
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在地域、时间、文化内涵以及制作工艺上都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卡若遗址距今有5300-4300年的历史,出土的陶片有2万余片,可辨认的器形有1234件。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的上限年代约为距今4000年,下限年代可能晚至吐蕃时期,器类有罐、钵、杯、碗、盘器座等,以罐为大宗,占可辨总陶器出土量的68%,各器皿外形生动且富于变化,主要用于盛器。
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基本上代表了西藏史前时期末期的陶艺水平,下面将从陶器制作的工艺特征方面对这两个遗址进行简单的叙述。
成型技术
卡若遗址的陶器均为手制成型,小型器物可能使用手捏成型,器形较大的采用泥条盘筑、泥片贴塑等成型。从最初追求陶器的实用性逐渐转为追求造型的艺术效果。
曲贡遗址的陶器也以手制成型,泥条盘筑为主,一些小型器物则是直接用手捏制成型,制作工序比较复杂,陶器成型后对接口沿和底部,圈足贴接器耳。
修整技术
尽管卡若遗址陶器的修整技术有慢轮修整工艺,但远不如曲贡遗址制陶工艺的轮修技术。器表多经打磨,但并不很光滑。
同卡若遗址相比,曲贡遗址居民拥有更高水平的制陶技术。不但绝大多数陶器的修整采用慢轮技术,而且采用“磨花工艺”,使陶器中的磨光工艺不仅是单纯的坯体表面处理,而且是一种器表装饰的特殊技术。这种技术将陶器表面打磨光亮后再磨出粗面做底纹,使保留下来的光面构成素雅的图案,这种装饰工艺在我国史前陶器装饰手法中是极为罕见的,是曲贡人独到的艺术创造,是藏族先民的特殊贡献。
纹饰
卡若遗址的陶器纹饰以刻划纹为主,常见的有回纹、单双波纹、平行条纹、菱形纹、连弧纹等。纹饰较丰富、规整不一、但不乏变化。纹饰皆在陶器的上半部分,可以推想当时人们把陶器直接放置地上,视觉角度只能看到陶器的上半部分。陶色有灰、红、黄、黑,以灰陶和红陶居多。
曲贡遗址的陶器纹饰丰富,分别有戳点纹、斜划纹、人字纹、平行纹、折线纹、弧纹、三角纹、V型纹、圆圈纹、网纹、菱枚纹、齿状纹。纹饰制作方法有刻划、压划、剔刺、雕塑、磨花。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器表一般以泥质和夹细砂陶罐的磨光程度最高,磨光不仅在陶罐口沿,甚至罐身内壁也被磨光。其中黑陶最多,制造也最精致,由于这种陶罐在烧制时要经过渗炭处理,所以表面乌黑铮亮。(
烧制
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烧制时温度不高,受热不均,以致器表颜色深浅不一,出现杂色。可推想当时尚未使用陶窑,人们只是在露天火堆里烧制陶器,很多陶器尚有烟熏的痕迹,可能大多为炊具。
曲贡遗址出土的陶罐使用高温烧制,烧制时经过渗炭处理,渗炭温度约为600℃—650℃,渗炭温度的变化使陶色也发生变化。
器型
卡若遗址的器类简单,器形的变化只与腹部最大直径的上下变化而变动,制作中较突出的特点是器表腹部最大直径处附加一圈泥条,泥条上饰压印纹。主要为罐、盆、碗三类器形,均为平底,其功能大多为盛器。
据考古资料表明,昌都卡若遗址有些器物上还有修补过的痕迹,在器壁的裂缝边缘可见当时修补时所穿的孔,有的孔还打在器底边缘,可见是当时常因失重而器底脱落。从这些修补过的痕迹中足以证明,当时陶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人们对陶器的珍爱。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双体陶罐”又称“刻纹双联陶壶”,高18.7cm,宽29.2cm,口径11cm,底径各为8cm。此罐质为夹砂黄陶,为双身联口形,圆口,口沿外翻,两腹为椭圆形,外侧各附一短钮,平底,颈部刻划双钩弧形纹,一腹部刻划双钩折线纹,另一腹刻双钩菱形纹,纹路之间空处以黑陶绘饰,故又称陶质朱墨彩绘双体罐。其造型独特、纹饰规整、蕴涵着创造者极其独特的审美情趣,是史前文物中的一大亮点。
但此罐的用途说法颇多,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单从造型上它就令后人充分遐想它所表达的内容和用意。有人认为,其形似双兽对立,且肩部的一对带孔器钮似动物的尾部。据昌都本地的民间传说:认为此罐与昌都的藏语名“”中第一个字母“”的造型完全一致,故此罐是仿字母“”所造。虽然这与文字起源的年代相差甚远,但也不失为一个神奇的巧合。
与卡若文化相比,曲贡陶器在制作技术上比卡若出土的陶器有进一步的发展,显示出更为成熟的技巧, 同时也体现了史前高原先民艺术思想的发展特点。
曲贡陶器的造型之丰富可谓高原陶器发展史上的颠峰时期,薄胎采用磨光制陶技术工艺,器形美观,纹饰精致,反映出很高的工艺水平,且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其中典型的有:代表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高原陶器艺术发展高峰的“黑陶单耳平底罐”(高17.5cm,口径8.6cm,最大直径16.5cm)和“黑陶高足单耳杯”(高11.5cm,口径12.4cm)等。
在博物馆内还可以观赏到其他遗址出土的陶器,其造型和装饰形成了各自独特风格,出现了不少造型新颖、装饰优美的生活艺术形象,由此可以直接领略到在史前青藏高原上的先进富丽而多元文化并存的特殊文化氛围与历史发展特征。
在西藏博物馆史前文化展厅,还陈列了当时制作陶器器表纹饰的各类工具。其中骨制和石制的梳形器,既简便又有极强的实用性,可在陶器表面简便地刻画出各种几何图形。梳形器也可以用来做皮毛和编制物的打纬器具,体现出人们爱美的天性以及对原始生产材料的驾驭能力。
由于陶器自身具有的特性和优点在当时被广泛运用,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先民们的生活方式,更记载了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状况,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和历史原貌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此外,由于空间与时间的不同,需要与追求的不同,标准与审美意识的不同,使陶器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与文化内涵,成为这个时代纵向断代和横向区分地区类型的标尺。从卡若出土的陶器和其他生产工具相对比,可以看出卡若文化并非是一种孤立的文化,而是与东面的雅砻江流域和北面甘肃、青海以及黄河流域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原始文化有相似之处,存在着密切的交流。
卡若遗址位于昌都以南12公里,在澜沧江以西卡若附近,海拔3100米的卡若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除陶器外在其它生产工具方面也能呈现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石器有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并存。
在建筑方面,不仅有房屋、炉灶、圆形台面、道路、石墙、圆石台、石围圈、灰坑等不同类型的建筑遗址,而且遗址密集错杂,左右相并,上下重叠,说明当时的建筑水平与技术已达到一定的程度。尤其是穴居、半穴居式的居住建筑,对藏区原始文化的建筑营造技术及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曲贡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代表着高原腹心地区一支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其器物造型对其后的雅隆部落直至吐蕃时期的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吐蕃时期的陶罐造型虽从总体上吸收了曲贡陶器的造型,但形态特征趋于简化,消失了很多曲贡陶器风格独特的造型。
无论是卡若还是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都离不开宗教的影响。作为藏区原始苯教等各类教义发祥和传播之地,青藏高原的很多遗迹中都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我们在某些陶片上看到涂有红色的颜料,有的陶器则用来装颜料,在史前红色被喻为生命与力量的象征,体现出藏族先民对生命的敬仰。因此,无论在石器、陶器还是在岩画上都有这种原始红色的暖色调,博物馆陈列室内还可以看到当时使用的色泽鲜艳耐久的矿物颜料。藏族先民认为通过宗教的祭祀仪式和各类祭祀物品,可以防范灵魂受到威胁。
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黑格尔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西藏的陶器文化与宗教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藏族陶器中不乏宗教题材的作品,先民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各类艺术形象,强烈表现创造者对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的追求。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伟大创举之一。陶器作为一种直接来自于生活与生产劳动的工艺美术产品,在其表现形式方面体现出藏民族特殊的哲学与美学思想。陶器的出现是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陶瓷器的国家之一,它对世界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它是远古先民们在与大自然的生存博斗中,以劳动、智慧与经验凝合而成的闪光结晶。究其起源,与多方面因素是离不开的,即人类又一次征服自然的标志,是对土的认识,对水、火的特性掌握,对物品贮存、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的需求以及对美的感性认识与再创造。这些就是促进陶器在人类生活中出现并日趋完美发展的主要因素。陶器的发明对远古人类的生活、生产及社会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随后出现的建筑、雕塑与工艺美术等文化范畴奠定了基础。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西藏古陶瓷文化,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也就是说,西藏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西藏发展史。
穿梭于这些质地迥异、器形丰富、色彩纷呈的西藏古陶陈列中,冥冥中仿佛立足于远古的史前年代,使参观者们充分领略到远古藏族先辈们在简朴而严酷的现实生活中,以坚强的信念、无比的智慧和顽强的斗志生存,并创造着与自然和谐相伴的文明那一凝重而绚丽的历史画面。
- 频道周排行
- 频道T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