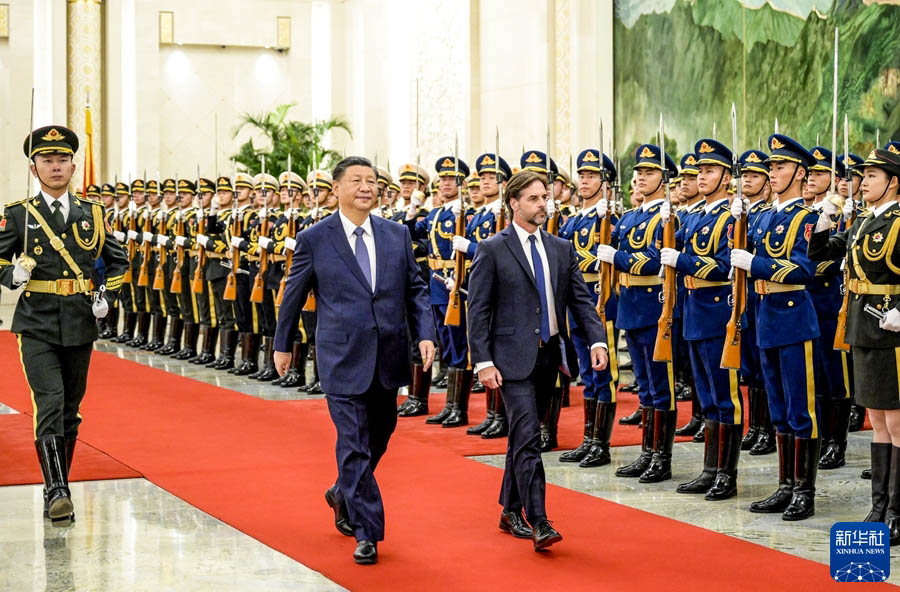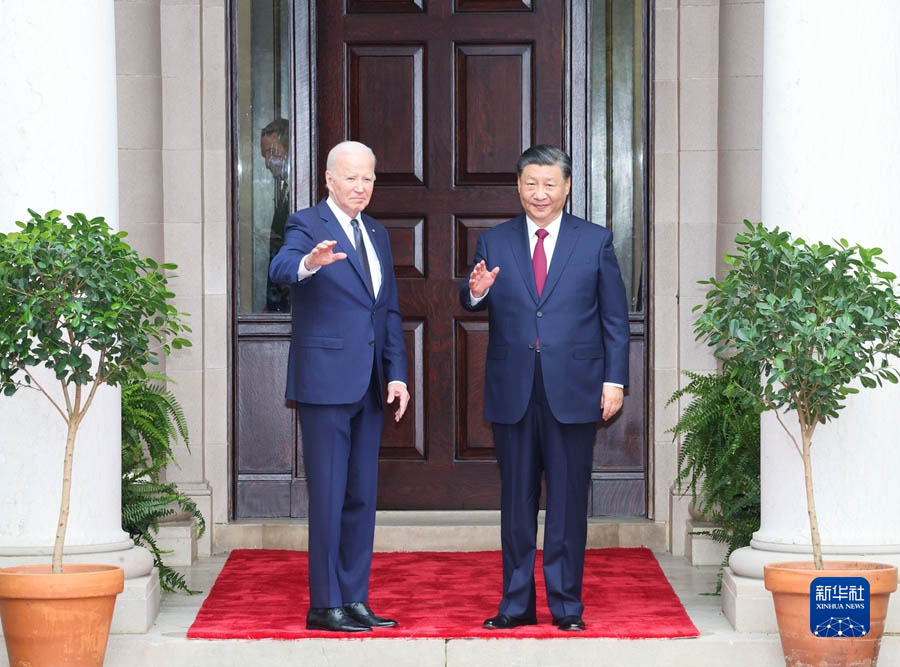清代康区藏族妇女生活探析
2014-03-14 10:17 来源:昌都报 点击:0
[关键词]清代;藏族;妇女;生活
[中图分类号]G04“214”=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5)04-0116-06
藏族是我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集中分布在今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西部广大地区,其悠久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然而,人们的目光总是聚集于历史舞台上的男性,妇女仅仅作为配角被随意地放置于历史舞台的边角。实际上,在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中,男性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藏族妇女在清代藏族社会发展过程中角色相当独特,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史料来揭示藏族妇女在创造藏族社会历史中的真实面貌。
藏族妇女的经济生活
有清一代,藏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社会经济在保持传统游牧经济的同时,一些地区已逐渐向农耕经济转变。而在藏族的农耕经济活动中,藏女不仅在田野劳作方面付出的劳动要远多于男子,而且还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甚至连传统的工商业也几乎成为她们的专利,史载:“平时操作,男逸女劳,稼穑耕耨外,妇女之力居多。主持家事,市茶布悉委诸女,供力役咸与焉。更有健于男子者,稍暇,携筠笼、捻毛线、织毪子,以供衣服。”这里的“男逸女劳”四个字,形象地刻画了藏族妇女在藏族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主角角色。近代以来,西藏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承担的角色,也令人闻之而愕然,史载:
西藏男子怠惰,女子强健。普通男子所操之业,在藏中大抵为妇女之职务,或耕作田野,或登山采樵,或负重致远,或修缮墙壁,建造房屋。凡普通男子所为,概为之。贸易亦多属妇人。且在家自疱厨纺织裁缝,及老幼之亦梳发等亦为之,并不以为劳,殆习惯使然。男子间亦耕作,不过为妇女之辅助,使牛马负载货物,亦非得女子之助不能,诚异闻也。
上述记载,虽然有其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性,但也反遇了清代在藏族广大的农耕地区,藏族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至少与男性一样担负着相同的角色和地位,即“男子所为概为之”。就劳动量而言,女性在户外付出大量劳动之后,还要承担所有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劳动。藏族这种男女劳动格局逐渐形成为历史积淀,即“殆为惯使然”。妇女在社会经济各方面担负的劳动强度均远远超过男性,“妇女和男子一样的劳动,她们比男子更能吃苦,较繁重的劳动几乎都是由妇女负担。”换句话说,藏族女性不仅主内,也主外。藏族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内外无别的角色意识与内地汉族女性是颇不相同的。在家务劳动方面,汉族的理想模式是“男耕女织”。而藏族却有反其道而行之的趋向,“西番妇女不操针黹,男子多腰小包藏针补锭,时则捻羊毛为线。”而在藏族传统的游牧经济中,女性也积极投身其中,据《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十“西藏”篇载:“大半为游牧之生活,逐水草而转徙于四方。虽妇孺小子皆从事于畜牧。”青海黄南藏族人民多从事农牧业生产,“妇女是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一切农活几乎都由妇女承担,男人除了犁地以外,最多在秋收、农忙时参加一些零星的劳动。牧业区,男人主要从事放牧。其他劳动都由妇女来干。……家务劳动也是妇女的事”。
商业贸易是社会生活中互通有无的必要手段,汉族的商业贸易主要由男人承担,而藏族的贸易经营却凸显了女性的主角意识,“其贸易经营,妇女尤多,而缝纫则专属男子。”乾隆刻本《西藏志·市肆》也载:“贸易经营,男女皆为,一切缝纫专属男子。”这与汉族传统农业社会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职业分配格局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职业格局与藏民自幼就逐渐培养的性别意识有关,藏族孩童稍长,“男子教书算,或习一技;女子则教识秤做买卖、纺毛线、毛氆氇,不习针工,不拘女诫。”藏族妇女在贸易过程中,不但坐贾行商,而且还充当中介牙人,“货物辐辏,交易街市,女人充牙僧,经纪其间”。女性能否善于贸易,甚至成为藏民判断女性是否贤淑的一个重要标准,“媳以善经营、能货殖者为淑。”在康定县出现了专门以女性经营类似旅店并代客商销售货物为特色的锅庄小姐:“本城原有十八家锅庄,凡康藏区商皆住此锅庄为旅店,不取宿膳费。盖客商之货交与主人代为贾卖,出入提取二分用代为膳费,形同内地之传统。凡营此者悉为女子,善为交际名为锅庄小姐。”清代汉藏边境贸易以茶叶为大宗,四川雅州府属的打箭炉厅“自改土归流,人烟辐辏,万商云集,尚为川茶入藏土产出口之商埠。”打箭炉为苛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乾隆《雅州府志》卷五《茶政》载:“炉不产茶,但系西藏总会口外,番民全资茶食,惟赖雅州府属之雅安、名山、荣经、天全、直隶邛州等五州县商人行运到炉,番民赴炉买运至藏行销。”在打箭炉的茶叶贸易中,一种名为“沙鸨”的藏族妇女非常活跃,客商的茶叶几乎都要经过其手才能销售出去,“打箭炉番女,年十五以上即受雇于茶客,名曰沙鸨。凡茶客贸易听沙鸨定价。直人不敢校,茶客受成而已。”由于藏族女性的勤劳,尤其在商业贸易交往中的善贾行为令人钦佩,嘉庆《里塘志略》卷上称:“贸易之事,妇人智过男子”。清代一些汉族商人在藏区从事商业贸易,并响应官府号召,并响应官府号召,在藏区报垦土地屯田,有些人甚至与藏族妇女组成临时家庭。又有“打箭炉汉民取蕃妇家于其地者,亦多从其俗,男犹汉服,女则俨然蕃妇矣。”
清朝藏族普通妇女有时还常常外出服役,“其差徭辄派之妇人。”藏族地区的关徭摊派,往往是男女一视同仁,“凡有生业之人,毋论男女皆派,即他处来者,或仅妇女,但能自立烟灶、租房居住者亦派。多寡各量其贫富不等。”藏族地区的摇役名曰乌拉,“至于土民之服役者名乌拉,凡有业之人,勿论男女皆与其选。”藏族妇女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行为,使她们就业的机会明显增加,“藏民体质强健,工作效率颇大,尤以女子为然。本县各种劳动工作,雇用藏民妇女,因时有间忙,价无一定,现在每日工价约有二角有奇”。与此同时,藏族妇女还在农闲时节,主动走出家门,到成都等地打工赚钱以帮补家庭生计,嘉庆时《锦城竹枝词》载:“北京人雇河间妇,南京人佣大脚三。西蜀省招蛮二姐,花缠细辫太多憨。(原注云:蜀中蛮人妇女,在省城内止肯雇佣,绝少卖作婢者)。”又载:“大小金川前后藏,每年冬进省城来。酥油卖了铜钱在,独买铙钲响器回。(原注云:蜀中三面环夷,每年冬,近省蛮人多来卖酥油,回时必买铜锣铙等响器,铺中试击,侧听洪音,华人每笑其状)。”同治《直隶理番厅志》卷四《夷俗》载:“诸番男妇于三冬进口,赴蜀西各郡县佣工,谓之下坝做活路。……春尽则贩卖缣布、锅刀、牲畜以归所。”对此现象,时人还赋诗:“熟生新旧聚三番,服语难同庶类繁,结队远行齐力作,雌雄难辨似猱猿。”下坝的藏民人数相当可观,乾隆时“杂谷等土司所辖蛮民家口数万山多地少,所产之谷,仅敷半年食用,每岁于九月收获之后,约计五六万口,皆入内地佣工。”相信这里一定会有不少藏族女性。
藏族妇女在藏族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极重要角色,并非在偶然因素所致,这与藏族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藏民“最信佛,家有二男,则一男为僧,有男女各一,则男子为僧,女子继产,女多而男少,故一切劳苦操作之役,皆女子任之。”由于藏民中的男性多信佛出家,在藏族地区的劳动队伍中出现“女子多而男子少”的现实,“故一切劳苦操作之役皆女子职之。”以此而言,藏族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独桃大梁角色的形成,也是由藏族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所决定的。
藏族妇女的婚姻生活
婚姻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单位,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也是与妇女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话题。清代藏族妇女由于在社会经济及家庭中的特殊角色,其享受的社会权利比汉族女性要高,藏族妇女可以像男性一样,享受财产继承权。在有几个儿子的家庭,家中的长子才有继承资格。实际上,若家中男性不出家,则由男性优先承继,老大藏名为“萨达”,他(她)既继承财产,又继承户名,若家有男女各一,而男子又为僧,财产则由女子继承。女性继承家产,从藏族的婚姻习俗中也可管窥一斑,民国《西藏志》记载:“如家中仅有一女,女之地位即较为强固。因其夫必须入赘其家,依妻之产业为生,取妻族之名字。妻本人,据藏人言,实为一家之根。父母死后,有主管家务之权。”藏族妇女在财产继承权上与男性享有平等的继承权,这与藏族妇女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分不开。
清代藏族的婚姻家庭也有较汉族文化独特的一面,其婚姻形态一般有三种形式: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家庭和一妻多夫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在三种婚姻形态中所占数量,“据估计大约有一半左右”。三种婚姻形式中的一妻多夫制家庭只限于兄弟共娶,并不是几个不相干的男子合娶一妻,这种婚姻家庭形式是以妇女为中心,“主妇自己住一间房,各夫轮流和她同居,不轮值的各夫或外出,或居另室,很少有家庭不和睦的事情发生。”从妻子享受的居住空间来看,藏族妇女在一妻多夫制家庭中具有较高的地位。据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记载,乾隆年间维西一带“兄弟三四人,共娶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玦,入房则系门,以为志,不紊不争。共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人如二妻。”藏族一些地区的习俗甚至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兄弟不和睦之表现,即使有身份之家,也实行共妻,“或独妻,则群谓之不友,而女安不许。以其地寒,不产五谷,乃如此……故土官头目,家非不裕,亦共妻。”这说明藏族一妻多夫制婚姻形式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有学者认为,一妻多夫制的婚姻形式同时可以减少人口的过度繁衍,但笔者在收集相关资料时并发现能证明此说的有力证据。在藏族所有的婚姻家庭形态中,“主持家务的都是妇女,她们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同时也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者。男子的活动常要受妇女的支配,特别在一妻多夫的家庭中,女权更要大些,子女都是听命于母亲。”因而,“西藏妇女之地位,由一方面观之,觉甚卑贱;由他方面观之则尊无二上,殆一家之女王也。日常自服劳动,自有财产,掌握一家之全权”。
女性在藏族社会经济生活中独当一面的优势以及藏族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形成了藏族社会流行“生育以女为喜”的现象。乾隆《西藏志·夫妇》载:“西藏风俗,女强男弱。……故一家弟兄三四人,只娶一妻共之。……其妇人能和三四弟同居者,人皆称美,以其能治家。”清代藏族地区的徭役负担多以家庭为单位摊派,而人户统计又以妇女为主,为了减少徭役负担,也导致兄弟共娶一妻之现象,“西蕃兄弟共娶一妇,生子先予其兄,以次递及。余询土人:番俗重女治生贸易,皆妇女主其政,与西洋同。计人户以妇为主,番人役重,故兄弟数人共妇以避徭役。”藏族徭役又多与住屋相联系,“番人徭役以住屋计,如三层、两层楼房者,徭役最重,平房次之,黑帐房又次之。”而一个成年已婚女子一般情况下,拥有一个家庭,由此推断,藏民的一妻多夫制在某种层面上又是为了减少所需住房的数量,从而也达到减少徭役的目的,减少家庭经济生活的压力,而且共妻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加强家庭内的团结合作。这些因素,最终形成了藏族“生女重于生男”之习俗。民国《西藏志》中对此现象也罗列了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说法与藏族地区真实的婚姻状况较为符合,即多夫制因恐家庭分裂、家产分散而设。多夫制之存在于藏族地区,实因其地土壤较贫瘠所致。同时藏族地区土地面积较广大,需要多人照管,这也是多夫制流行的一个因素。
藏族妇女在繁荣藏族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贡献巨大,由此也造成藏族男女在婚姻选择上,那些善于理财经商的女性,更被男性看重,“藏民上等社会之风俗,必择门户,男子以识字为佳,女子以善贸易识物价理家务为善”。这在乾隆《西藏志·婚姻》中也有类似记载,“男识字者佳,女以善生理识货价理家务为善”的局面。
通过婚礼中的一些仪式,我们还可以管窥藏民男女在服饰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男穿大襟小袖以皮褐为衣,女则短袄长裙足穿皮底袜,男多佩刀,男女俱持素珠,风俗男女无别。”在藏民的婚宴中,“男女相娶同坐,彼此相敬,歌唱酬答,终日始散。男女团聚,手趺坐而歌,至于门外,歌唱于街中而散。”《西藏图考·颜检卫藏诗》记载,婚宴过后,便出现“引袂杂男女,踏歌非醉颠”,或是“男女盛饰,群聚歌饮,带醉而归,以度岁节”的景象:
夷俗每逢喜庆辄跳歌妆,自七八人至一二百人无分男女,附肩联臂绕迳而歌。
同治《章谷屯志略》载,藏民婚礼宴会后,“男女数十百人联臂呼躩,跳歌妆以为戏。是日夫妇不同室,越日妇随姐妹回母家,为作如初。婿家则日月至焉,而已及翁姑授以家事或生子女后则长依婿操作。”即使在婚娶期间,女家也处于较高地位,藏族男女多为自由婚配,“男女率先私合,然后婚配。男家请喇嘛拣择吉日,通知女家,至期,两家各延喇嘛诵经礼忏,亲戚邻里,咸集女家。”在妇家摆婚宴酒店,男家请一人往女家参加婚宴,其间,“男家人长跪而后饮之,妇家者端坐不动也,饮毕,群拥新妇至夫家。”在婚礼宴会上,女方可以“见舅姑不为礼,依母家女伴同饮。”显示了女性及其家庭的尊贵。
爱着是女性的天性,藏族妇女同样也有爱美之心,“番女涂面多用孩儿茶亦有用葡萄捣和涂泽者,云避风日,如中华之施铝粉也。水洗之后亦多洁白。”这些美容习俗甚至连汉女也效仿,“西藏妇女以糖脂涂面,初以为怪,嗣在云南缅宣见有以草染齿如漆者,询之则意在贡媚也。别觅一草洗之,其白如故,华人亦效之。”
可见,在高原文化背景下,清代藏民在婚姻礼节上表现的男女双方同坐、同饮,甚至男女在歌舞中相互嬉戏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男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这与汉文化历来强调的“男女授受不亲”有巨大反差。
藏族妇女的政治生活
藏族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政治上基本实行的父系继承制,以父权为大,并以法律形式约束妇女,规定“不听妇人言”,“妇女不准参加盟誓会广议”等,约束妇女参与政事。“家庭在分工上,男子主要负责与政府和宗教交往方面的事务,其余财产的管理,社交来往等都由妇女负责,在宗教活动上,妇女的地位是比较低的。”但事实上,由于吐蕃时期宫廷中的女性平时要协助男性的赞普和大臣们处理社会经济诸公务,难免不涉及政治生活,尤其在紧要政治关头,还会出现女性执掌权柄的现象。
女性在政治关键时刻执掌权柄的现象,至清朝受到官方的认可。《大清会典事例·兵部》卷五八九记载,清代对土司承袭规定:承袭者首先是嫡子嫡孙,无嫡子嫡孙者,以庶子庶孙承袭,无子孙者,以其弟或族人承袭,族无可袭者,或妻或婿有为“土民”所服者,也准承袭。这一规定其实为女性承袭土司一职提供了法律依据。藏族妇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承袭土司一职,成为管理本地民众的首领,藏族称之为女士官。嘉庆刻本《西藏纪述》中记载了四川雅州府属董卜宣慰司与明正司在康熙、雍正时期土司职承袭情况。康熙元年清政府颁给董卜宣慰土司印信,康熙 四十九年该土司“出兵宁番,在事身故”,其子坚参达结年幼“不能理事”,由“其妻桑结护理印务”。而明正土司噔争吒吧印信是康熙五年政府颁发的,康熙二十年噔争吒吧病故,子蛇蜡查吧承袭,康熙三十九年蛇蜡查吧意外死亡,因其乏嗣,“其妻工喀以继夫职”。后工喀病故无子,工喀侄女保女也于康熙四十一年身故,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七年颁发印信给桑结,令其视事。四川巡抚年羹尧对此上奏,“河西宣慰司故土官蛇蜡喳吧之土妇工喀病故,并无应袭之人,请将蛇蜡喳吧嫡女桑结承袭。应如从请,从之。”雍正三年,打箭炉发生地震,土司桑结被压身故。其儿子坚参达结于该年承袭了董卜宣慰司的职务,雍正七年又因“明正员缺,无亲支族舍可以议袭替”,“请以董卜宣慰司坚达结兼袭母职”。雍正十一年二月,坚参达结病故,以长子坚参囊康承袭董卜宣慰司职务,因其“年未及岁”,“印务暂令坚参达结次妻王氏幺幺护理”,并以次子坚参德昌承袭明正司,同样因其年幼,又由坚参达结之妻喇章署理,喇章乃小金川土司汤鹏之女。
上述的式喀、桑结、喇章、王氏幺幺四位妇女,其中明正司女土司女官工喀因夫死乏嗣而继夫职,随后因桑结乃其夫侄女之女而继明正司一职;另桑结又与喇章、王氏幺幺两儿媳皆因其丈夫身故,子尚幼而先后掌管地方土司印务。与此可见,清代藏族社会的政治权力仍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妇女们只能在其夫死后且缺乏后嗣或是无后嗣的去世土司属近亲关系的情况下,才可担任土司一职。特别是桑结在护理董卜宣慰司印务同时,还以其亲属身份袭举明正司一职。当然如身故土司有子则由子继承,子若年幼,则先由其妻代为护理印务。这一现象在藏族地区较为普遍,乾隆年间,明正、木坪两土司,各因其子年幼,皆系土妇任事。但不管怎样,藏族女性还是在政治舞台中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凡土司死或其子尚幼,则其妻暂行袭职,谓之土妇。明正土妇工喀乃宣慰司蛇蜡吒吧之妻,于康熙五年归诚,即今土司甲木恭语尔布之祖母也。里塘亦系土妇名阿错,乡蟒数珠帽上缀以红顶,迎送拜跪与土司无异。
藏族传统的游牧生活,决定藏族传统文化的崇尚武力,女性对此耳濡目染,也养成好武之习俗。“夷谷尚武,咸工击刺之术。虽妇女亦解谈兵。”女性甚至也可以编印兵治理一方,“崇化属之独角寨屯千总肯朋死,子幼,其妻板登尔跻摄职,抚治番民,岁时随各屯弁参谒。服男子顶带。”这一史料透露了藏族妇女尽管可以主政,但男权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女性,所以板登尔跻要“服男子顶带”。但在同时期的汉文化中,男权社会中的妇女是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即使子幼,汉族女性最多也只能躲在幕后垂帘听政而已,女性根本不可能走到政治舞台的前方。而藏族女性在特写的条件下则可以享受土司继承权,并受到法律保护,妇女的政治生活空间得以延伸,可以与男性一样行使土司职权。当然,这些妇女是清代藏族妇女中的特殊阶层,而她们所参与的各种政治活动,也成为这一阶层妇女政治生活的代表。
即使在宗教信仰方面,藏族女性同样也可以与男性一样享有平等的出家权利,虔诚地践行着自己的宗教信仰,“藏民笃信佛教,民生子女,出家者居多数,男子为喇嘛,女子为觉魔子,犹如比丘尼。”《西藏纪游》卷二也记载:“番中女尼号觉母子,自藏以西多有寺院,亦有耕种为业者,遇官差仍供乌拉也。浪噶考有江珠胡图寺在海子边,相隔巨浸约二十余里,亦觉母女尼也。”而子女较多的家庭也一定会让其中一二人出家,“凡儿女有三五人者,必舍一二以为僧尼。”同时在藏族的宗教事务者,女性甚至还可以晋升为住持,金川的“勒乌围,旧有喇嘛寺。女喇嘛主持,能先知未来事,为夷人推信。”
综上所述,有清一代,藏族妇女在社会经济、婚姻家庭及政治舞台等各方面均展示了女性的风采。在藏族性别文化观念中,没有汉族传统文化强调男女性别的主从观念,也没有汉族士大夫们制造出来的对女性的种种行为规范,女性在藏族社会经济生活中承担了应有的角色,由此也给她们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本文责任编辑 季垣垣(特约)]
[作者简介]刘正刚,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敏,暨南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广州 510632)
- 频道周排行
- 频道T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