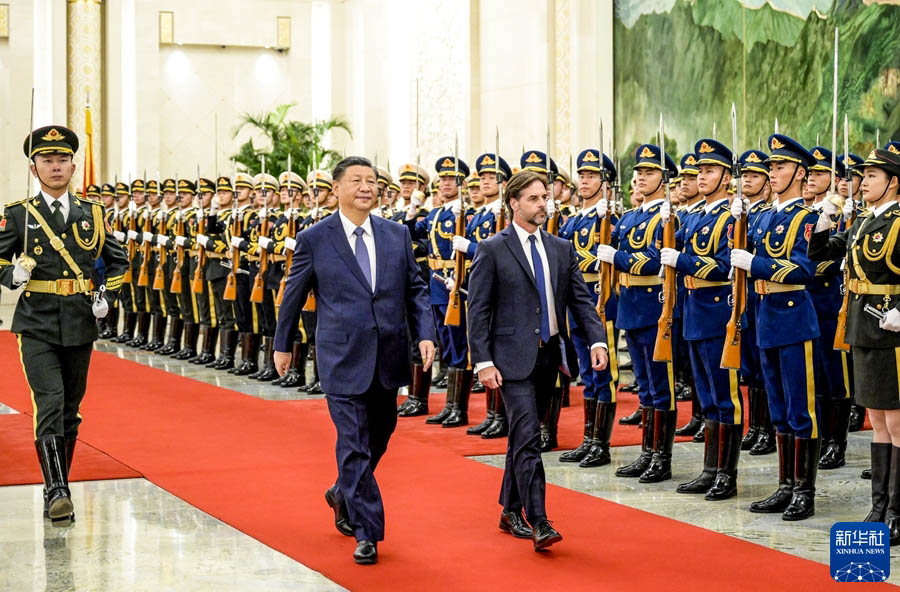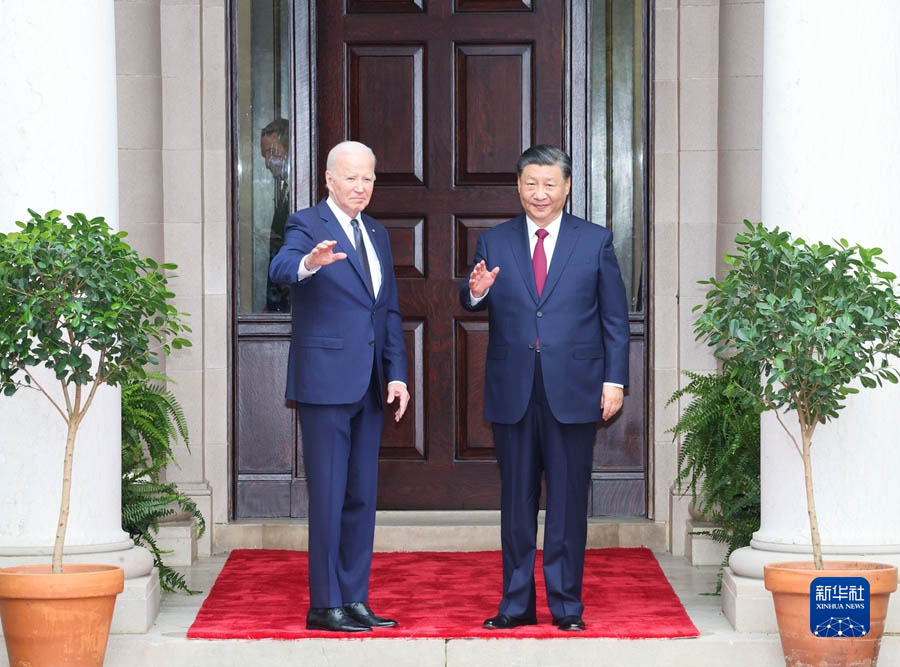刻进了生命的丰满岁月
2019-11-25 08:21 来源:西藏日报 点击:0
记者手记:
10月22日,西藏日报刊发了《养好路、护好路,才能让党放心!》一文,讲述退役军人次军坚守唐古拉山养护段近20年的故事。10月23日一大早,记者突然接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电话:记者同志,我是次军的老排长啊,我们断联系十几年了……老排长话语激动,夹杂着欣喜、期盼。
这一通电话,开启了一段青春属于西藏的情怀,也带记者走进了这个特殊的群体:那些把青春奉献给雪域高原,而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老西藏”们的故事。那是一段——刻进了生命的丰满岁月。
他们在西藏的年头,短的不过匆匆几年,长的却是整个青春年华,或长或短的情缘却刻下了他们一辈子的印记:老西藏!
关于西藏的记忆,握得再紧,也在时光的指缝里一点点流逝,但他们始终忘不了入口第一丝青稞酒的甘甜,忘不了第一次嚼糌粑团时的干涩。
那是西藏的味道,如何能忘。
他们说,脚下曾经踏着的那片土地叫“故乡”,额头轻碰过的那个同胞叫“亲人”,魂牵梦绕的那份思念叫“情结”。他们的西藏岁月和用无私奉献谱写的老西藏之歌,至今依然在雪域传唱、在高原回荡……
(一)
陈钦甫最后一次回西藏,是2001年,与老伴陈波一起。飞机在林芝机场稳稳落地,陈波的心跳却骤然快了几拍,从1957年离开,无数次入梦的那片波密原始森林、那座翻了一天一夜的大雪山、那块扎下新婚帐篷的草地……此刻,就要在眼前了。多少回忆涌上心头。
陈钦甫当时不知道,那是老伴离开西藏后第一次回去,却也是最后的一次。
1950年,17岁的陈钦甫从豫皖苏革命老区来到大西南,作为徒步进藏的一名十八军战士,从捏着鼻子“灌”酥油茶到用藏文丝毫不差地写下《十七条协议》, 不过半年光景。这半年波密分工委一边做统战工作,一边开荒生产:“为了在西藏站稳脚跟,部队必须先要自给自足。每个战士每天需开荒半亩地,这是硬性任务。”第二年春天,2000亩新开垦的土地上洒下了青稞、小麦和蔬菜的种子,秋天里那满仓的粮食加起来足足20万斤。战士们徜徉在丰收的喜悦里:从此 “就要在高原安家了”。
十八军扎下了根。陈钦甫和爱人陈波也在西藏扎下了根。松明子灯下,拿着棍子在地上学写藏文,熏得脸黑鼻孔黑;在藏族群众家里学藏语,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作。
昏暗的油灯,和着木屋缝里揉进的月光,同住的藏族阿妈啦一家哼起了歌儿,陈钦甫的小提琴伴着奏,那个酥油飘香的夜晚,每每穿过记忆来入梦。那是一段物资异常贫瘠精神却格外丰满的岁月,不知不觉刻进了生命。
1957年,陈钦甫接到任务:带领60名藏族学员到西藏团校(今西藏民族大学)学习,从此他和爱人把一辈子献给了这个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西藏干部人才的热土。
(二)
“献了青春献子孙!”
7个字,沉甸甸的却是一辈辈“老西藏人”最无悔的付出。
范亚平,54岁。祖孙三辈12人中,有11人曾经或现在依然在西藏工作。
1957年,范亚平毅然放弃了原本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成为进藏的第一批大学生。至于为什么,范亚平老人想或许是弥散在记忆里的西藏许许多多的好吧!
1956年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大三的范亚平受聘到西藏调研,拉萨至日喀则尚可坐车,之后就是骑马、坐羊皮筏子,一年的调研花了一半时间在路途上。
在一个调研点,同组的学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高原反应,她们只得请求借宿的藏族阿妈啦:请帮我们烧一点开水。二话没说,白开水、酥油茶,甚至还有干果、小点心,很快都端了来。临走时,范亚平他们要给钱,阿妈啦却生了气:回家住还要给父母拿钱吗?你们见外了。
也许正是那句“见外了”,种下了范亚平和西藏的情。又或许是在拉萨一小实习结束前,孩子们拉着她的手恋恋不舍时,范亚平无心的一句承诺:你们放心吧,我们还会回来的。
回来西藏的,不仅是范亚平和爱人韩兰勋,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祖孙三辈12人中,除了孙辈中有一人在北京工作外,其余11人都在西藏或者与西藏相关的地方工作。
回来西藏的,还有陈钦甫老人的后代。陈钦甫夫妇一生养育了两个女儿,成人后也先后送到西藏“上山下乡”插队锻炼。
(三)
像范亚平、陈钦甫这样的家庭在西藏千千万万。为了西藏的解放、建设和发展事业,一代代人前仆后继,在高原扎根生活。
守卫边疆、保卫国防!“老西藏精神”就是这样在几辈人、几代人的牺牲和付出中得以延续!
坚守的是根,是一个叫“老西藏精神”的魂。
哪怕不得已离开,也断不了“老西藏人”的根。
1979年,甘肃柳园。接到西藏广播电台聘任通知的陕西人高有详带着简单的行李,幸运地搭上了一辆前往拉萨的顺风车。
蹬着自行车、手拿索尼牌小录音机,是80年代电台记者的“高配”,一边当播音主持人一边采访,怀着火热的心高有详写了100多篇关于新西藏建设、发展的稿子。
“那时候基本没啥蔬菜,肉是限量供应。单位每次有人休假回内地,都要想方设法带一点蔬菜和水果回来。一到周末,闻着哪家的蒜苔腊肉香味,一群人钻进去蹭饭。”回忆带着香味,飘散不去。
1988年,病中的母亲无人照顾,高有详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回到陕西。十年的高原记忆从此再难忘。
难忘西藏的又何止高有详一个。
1997年,从军校毕业的叶常学写了个申请:自愿到西藏。
这是他第二次到部队。最初新兵蛋子是在东北那个极寒的吉林,三天两夜的火车。第二次却是高原上的西藏。叶常学默默地说:对自己可真够狠。
那时到西藏,可以到四川坐军航。这对来自重庆铜梁农村的叶常学来说很“洋盘”。可这军航也不是好坐的,一等好几天,里面还有货物,噪音又大、又冷。
到达拉萨后,叶常学没有别人说的“走路都喘气”,却有一番心旷神怡。从此他乡成了故乡。直到2015年叶常学自主择业回到家乡,整整18年。
已过不惑之年的叶常学常感慨:小时候的记忆已然不多,而今最多的记忆、感情都留在了西藏。也是在那段岁月里,次军成了他带的新兵连里最普通的一名新兵。
……
青春已逝,岁月如歌。
常能响起耳畔的只剩下只言片语了。
“本布啦(意为领导),您睡在中间,我们在外面守着”,野外修路时,怕晚上有野兽袭击,藏族同胞把陈钦甫护在最安全的位置。
“你是我在西藏交往的第一批汉族好朋友”。病床上,江中·扎西多杰拉着陈钦甫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下了这句话。
“莫萨,别怕、别怕,你的马儿回来了”,那个从远处一手拿着手纺车、一手牵着受惊走失的马儿的“波啦”,在哭得泪眼模糊的范亚平眼里,格外温暖,格外亲切。
西藏,一旦相见,今生再难相忘。
- 频道周排行
- 频道T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