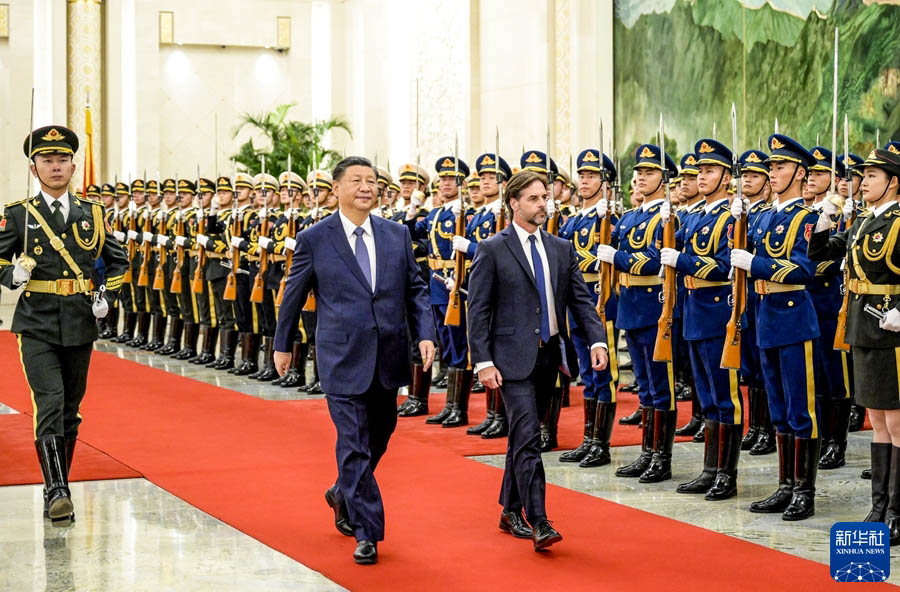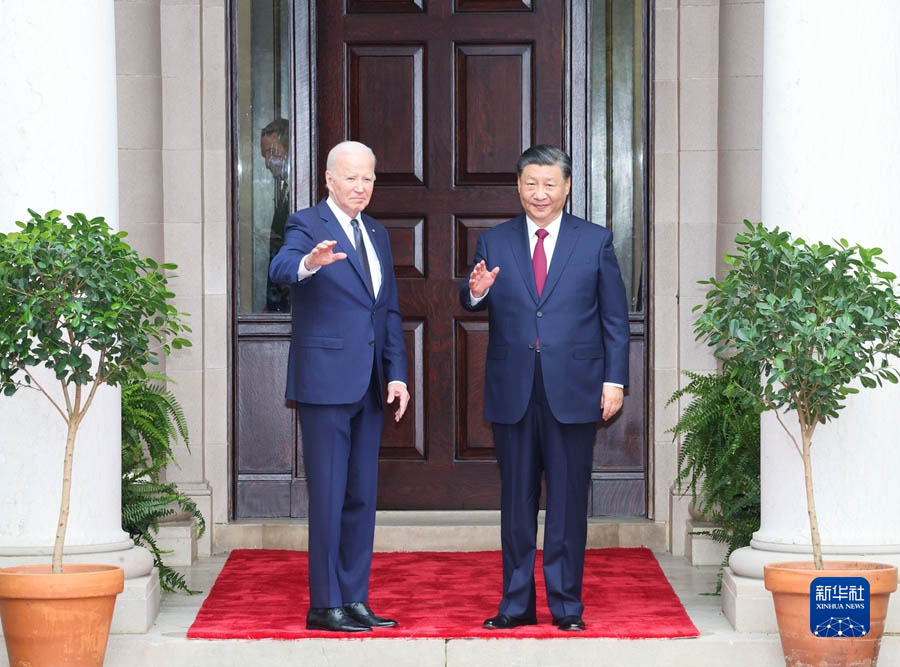杜永彬:西方社会对西藏存在五大误读
2014-03-13 21:53 来源:西藏新闻网 点击:0
文章指,一些西方人在看待西藏文化时,只是要求保持其多样性,不愿看到西藏文化的发展和适应现代化;还有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这个世界人口大国的国情,他们把与中国其他省区一样的西藏的正常人口流动说成是国家有计划的人口迁徙和汉化西藏。他们夸大和看重藏族、西藏和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及其与汉族、中原和汉族文化的差异和对立,缩小甚至忽视藏汉民族的共性、友好和相互认同。
文章建议,“百闻不如一见”,西方人只有去西藏亲眼看一看,才能了解和认识真实的西藏。
杜永彬先生长期从事西藏研究,先后5次应邀来哈佛大学等学术机构参加有关西藏的学术研讨会,曾受聘为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杜文从历史和现实、东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系统、客观地剖析了西方世界对西藏误读的根源,值得一读。
西方人有一种独特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文明神秘而玄妙。作为东方文明的一朵奇葩,西藏文明不但令西方人魂牵梦萦,也让他们难测高深,几个世纪来,西藏壮美雄奇的自然景观和神秘神奇的人文景观和西藏文明对西方人一直具有魔幻般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人。由于地理、文化和语言的阻隔,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雾中花,水中月,难见本质和真谛。这反而成了西藏对西方人的吸引力和诱惑力,由此而使西方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西方人了解西藏和认识的主要途径是:以英文为主的西文文献;流亡藏人的作品和“现身说法”;有关西藏的展览、音像、影视,各种有关西藏和藏学的会议,其中,西方传媒在塑造西藏形象和西方人的“西藏观”中起了十分独特的作用。
西方人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以及他们了解和认识西藏的途径,必然会导致其对西藏的误读。
一、西方对西藏误读的几种表现形式
1、对西藏概念的误读 。
在西方的出版物中,西藏(Tibet)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藏文古籍中早就清晰并沿袭至今的三大藏区---卫藏(法区)、安多(马区)、康巴(人区)不加区分,也不顾及传统的行政区划和藏族聚居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五省区的现实,在论及安多和康区时,几乎都以“东藏”(Eastern Tibet)相称。这种并不存在的“大西藏”概念,造成许多误解,仅汉文翻译就成问题,究竟是译成西藏、藏族还是藏区?
2、对藏民族的误读。
近东研究专家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人的想象被作为与任何非欧民族和文化进行比较时的权威标准。此外,还有一种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的霸权,他们自己反复申明先进的欧洲人对落后的亚洲人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一些西方人实际上是带着“东方主义”的眼镜审视藏民族和西藏的。正如流亡藏人学者降央诺布在《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一文中所说,考察有关西藏的游记及关于西藏宗教和“文化”的大量“新时代”风格的作品,给人们留下不舒服的感觉,自从詹姆斯o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和洛桑然巴的《第三只眼睛》这类书籍提供了关于西藏的有益文学主体以来,西方人的西藏观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影片中出现的西藏,要么是一种最终的精神庇护所,如像《千禧年》、《危险边缘》和《幺点冒险――当大地呼叫时》中所表现的,要么是一种魔幻力量的储藏室,如像《通往香港之路》和《阴影》中所展示的。西藏被视为西方的“他者”。
西方人,无论其有怎样的过失,都是真实的;西藏,无论多么精彩奇妙,都是一个梦幻——不是一个消失已久的黄金时代,就是太平盛世的幻想,仍然只是一场梦。在每一次这样的表述中,西藏人或他们的家乡和文化充其量只是充当一个背景或衬托白人主角的更为重要的工作,有一个固有的和潜在的前提是,假如西藏为西方人的目的和需要服务的话,她仅仅是相关的。在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中,主角康韦是英国人,为首的喇嘛是欧洲人,就像大多数香格里拉的高级官员一样。西藏人基本上都是迷信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伐木工和抽水工,在香格里拉的白人精英看来,都是一些苦力。
3、对西藏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误读。
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的现代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潮流。怎样在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是每个族群和美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矛盾和挑战。一些西方人在看待西藏文化时,只是要求保持其多样性,不愿看到西藏文化的发展和适应现代化。其实对现代化有些腻味的西方应当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地球上的任何族群(当然包括藏族)都有权利分享人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带来的成果,这是“天赋人权”!一些西方杞人忧天,担心青藏铁路会危及西藏的传统文化。殊不知,西方人都不愿坐火车了,而一些藏族百姓做梦都想在有生之年能看见会奔跑的“铁龙”——火车!
4、对藏传佛教误读。
一些西方人在观察西藏同中国内地、藏族和汉族时,有一种探求差异、忽视共性的嗜好。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和传播,形成了两大传播体系,即上座部(俗称小乘佛教Hinayana)和大乘佛教(Mahayana),在东方佛教界和佛学界,将传播到中国(包括藏区)和日本、盟国等国的北传佛教称为大乘佛教,将传播到斯里兰卡、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称为小乘佛教。而西方人却将与汉传佛教同属大乘的藏传佛教分离出来,单列为与小乘、大乘并列的“金刚乘”(Vajrayana),如纽约就有一种佛教刊物《三乘:佛教评论》(Tricycle: Buddhist Review)。
而且,部分西方人误以为藏民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和奉行非暴力的,如果他们稍微读一点西藏历史就会知道,即使在全民信教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一些贵族并非真正的藏传佛教信徒,否则怎么理解好几世达赖喇嘛都因被毒害而夭折呢? 美国学者洛贝兹(Donald S.Lopez,Jr.)对此也有论述。
部分西方忽视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的并存的实事和不同教派之间的差异,将只是格鲁派大活佛的达赖喇嘛视为整个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并且,一些西方并不完全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达赖喇嘛的身份和国际形象已发生了变化,扮演着宗教和政治双重角色:不仅是大活佛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还被奉为流亡藏人和一些西方人的精神领袖,能言善辩的外交家和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他已将藏传佛教政治化,将藏传佛教的教义伦理道德化。
5、对西藏政治和中国西藏政策的误读。
虽然迄今为止所有西方的官方文件都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一些西方议员和官员却从喜欢打“西藏牌”,图谋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甚至将其作为分化和肢解中国的突破口。因而认同和支持西藏独立,将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视为国家关系。他们不顾历史事实,主观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1951年进军西藏和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对西藏的占领和侵略,现在西藏仍然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达赖喇嘛是西藏国的国家元首,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见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
一些不了解西藏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受西方一些传媒和政界的影响,也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些西方人对藏族及其与汉族的关系也存在误读,他们忽视自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和唐朝以来藏汉民族之间团结友好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夸大了藏汉民族的对立和冲突。
事实上,自古迄今,团结友好一直是藏汉民族关系的主流,彼此通婚联姻的传统佳话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起延续至今,不胜枚举。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藏汉民族的关系是十分友好亲密的。一些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西藏政策,假如他们真正把握了中国在西藏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统一,也许就不会提出西藏的民族自治,困扰接触商谈的“大西藏”问题也就不会成为难以解开的结了。还有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这个世界人口大国的国情,他们把与中国其他省区一样的西藏的正常人口流动说成是国家有计划的人口迁徙和汉化西藏。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藏民族也在不断地向中国内地的大都市流动和定居,近30年来,从西藏和四川藏区流动迁移到成都市辖区的藏族人就有10多万,北京也居住着近万名藏族人。
西方人误读西藏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对西藏的误读,西方人的西藏观和西藏形象,许多都是虚幻的和不准确的,对西方民众对西藏的态度和西方政府对西藏的政策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其结果不但歪曲了西藏和中国的西藏政策,也误导了流亡藏人和西方民众,对“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和西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人对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偏爱,“爱屋及乌”,进而喜好西藏文化、崇拜达赖喇嘛、热衷于达赖集团的“藏独”事业,加上西方传媒对“西藏问题”的炒作,促成了西方人的西藏观“一边倒”。
一些西方人由对西藏文化的兴趣,转而关注“西藏问题”,热衷于“藏独”活动。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o瑟曼,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o基尔,著名电影导演马丁o斯科赛斯等,改宗藏传佛教,皈依达赖喇嘛,成为其忠实信徒,竭力支持达赖集团的“藏独”事业。一些西方人受误读西藏的影响,带着同情弱者的心理,即使对西藏和“西藏问题”一无所知,只要流亡藏人鼓动的活动,他们都盲目参与。
二、误读西藏的主客观原因
大多数西方人之所以误读西藏,既有历史和现实的根源、东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也有主观和客观原因。
一是,西藏信息源的缺陷。
上述西方了解和认识西藏的主要途径中几乎都是间接渠道,而没有中国这条直接的途径。对于包括藏族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关于西藏的论著和中国传媒关于西藏的报道,西方人知之甚少,这显然是信息不对称。个中原因是:大多数西方人都不懂藏语文和汉语文,而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报道又以藏文和汉文为主;关于西藏的材料、知识、信息和看法主要是由西方传媒和学者提供的,多数西方人是通过间接途径或第二手资料了解和认识西藏的,到西藏实地考察和亲身体验的西方人并不多,以电影为例,据统计,国外有关西藏的影视片262部,其中达赖方面占133部,关于达赖的有39部,大部分拍摄于1980年代,中国拍摄的只有9部,占3.2%,因而西方人所看的有关西藏的电影大多数都是西方人在中国藏区以外拍摄的,这就决定了西方传媒所反映或表现的是“西方的西藏”。
二是,认识和价值观因素。
一些西方人夸大和看重藏族、西藏和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及其与汉族、中原和汉族文化的差异和对立,缩小甚至忽视藏汉民族的共性、友好和相互认同。许多西方人并不知道,藏族和汉族有共同的信仰---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藏族的本土宗教是苯教,汉族的本土宗教是道教,而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属大乘佛教;并且,自吐蕃王朝和唐朝起,藏汉的佛教文化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藏族喇嘛东传与汉族和尚西取,仪轨同奔,谱写了藏传佛教东渐的壮丽画卷。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向中原的传播和发展,既表明了藏族的向心力和藏族文化的内向发展,也表明了汉族对藏族、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接纳和认同。而且,藏医和中医有很多相似之处,藏医是在吸收了中医和西域医学的一些合理的成分中形成的,藏医和中印在望闻问切的治疗方法和医学理论上都是相通的;借鉴了汉族农历的藏历,其“五行”、十二生肖和六十甲子(绕迥)与农历也是大同小异;藏语文和汉语文同属于汉藏语系。
同时,一些西方人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动态的西藏,他们的西藏观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多大的变化,而西藏却在紧跟时代的脚步飞速行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西藏观显然难以准确地反映真实的西藏。
一些西方人还用居高临下的视角俯视西藏和西藏文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当西方的工业化尚未完成、现代化正在迅猛发展时,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具有一种种族优越感,怀着“西方中心论”和俯视的心态观察西藏,其言辞充斥着对西藏和藏族的贬低甚至诬蔑,瓦德尔(Waddel)的《西藏的佛教和喇嘛教》就是明证。20世纪中叶以来,进入“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西方在反思现代化时,才认识到了理性、科学技术和物质主义乃至西方宗教并不是万能的,难以应对他们遇到的许多现实问题,于是一些西方人将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和宗教,尤其是对注重精神的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情有独钟。这时,他们带着朝圣心态看待西藏,将西藏、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神化,出于“自助”(self-help)的心灵需要,制造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香格里拉神话”(Myth of Shangri-La)。美国人罗伯特·瑟曼和理查·基尔将藏传佛教奉若神明,瑟曼将藏传佛教称为“内心的革命”(Inner Revolution),理查·基尔声称在物质主义至上的世界幸亏还有藏传佛教。
三是,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
与西方普通民众对西藏误读不同的是,少数西方人戴着意识形态的眼镜和“冷战思维”观察社会主义中国,他们感兴趣的不是西藏而是关注“西藏问题”,他们只看到西藏的离心力,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西藏的向心力;他们只希望西藏缓慢发展甚至保持原样,不是真诚地希望作为56个民族和30个省区之一的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一道和睦共处,共同走向繁荣;他们还武断地将中国传媒对西藏的介绍和中国学者对西藏的研究都视为宣传。
四是,语言障碍。
由于大多数西方人都不懂藏文和汉文,自然也就难以了解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西藏观。美国藏学家史伯林(Elliot Sperling)认识到了这一局限,他认为,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关于西藏的研究成果了解不够甚至轻视,不但导致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误读,也导致美国西藏政策的失误。他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除了对人权问题进行更广泛的思考,还不断深化对西藏人权问题的怀疑和评论”。“应当通过研究汉文文献来看中国处理西藏人权的方式”。“美国政府确实是在关注西藏问题,但是也暴露出它对中国在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西藏问题上的复杂立场不够熟悉和了解”。“理解中国人发表的观点的实质对于我们是十分有益的。因为中国人的观点并没有受到中国之外参与讨论这些观点的学者的重视。西藏流亡政府定期出版一些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的这类英文文献,但是并没有涉及汉文文献中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观点”。“1998年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之前,就遇到了一次彻底的失败。当时西藏流亡政府驻华盛顿的代表宣布西藏问题即将获得突破性进展;实际上,对中国的政策误读已经渗透到克林顿政府中去了”。“显然,对中国西藏政策的理解需要对包含在这些文献中的内容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参与西藏问题研究和辩论的人们对上述文献完全理解之后,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一些错误认识才会逐渐减少”。
五是,精神的需要。
一些西方人将雪域西藏视为人间的“最后一片净土”,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他们出于“自助”的需要,仍然幻想从自然和人文方面保持西藏的纯洁性,实际上是要满足其身心的需求:信仰、探险、旅游、休闲、健身,以缓解竞争的压力,慰藉空虚的心灵。降央诺布说,“香格里拉”的幻想主要与西方一些人的感情需要有关。这也正是梦幻般的“香格里拉”对许多西方人的吸引力和诱惑力所在。
三、了解西藏还应“眼见为实”
应当看到,在西方普遍误读西藏的格局中,还是有一些正读西藏的西方人。20世纪中叶以来,尽管“冷战”和“后冷战”的国际背景的影响,但是西方人当中还是有一些对中国西藏较为友好的有识之士,如早年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韩素音、爱泼斯坦,以及奥克森伯格、谭·戈伦夫、戈尔斯坦、弗里曼等。而且,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一边倒”的局面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形象的改善、国际威望的提高、国际作用的发挥和中国西藏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变化,随着“西藏问题”的发展演变和国际形势的跌宕起伏,一些西方人认识到了客观公正地认识西藏和“西藏问题”的重要性,也符合西方人及其国家的利益,意识到了对西藏的误读,并在加以矫正。西方人的西藏观也在发生变化,对“西藏问题”和中国的西藏政策的视角,从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从“冷战思维”转变为较为客观公正。
西方人对西藏的误读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对西藏的神秘感,导致西方人对西藏文明讳莫如深;由于情感上的距离和政治上的偏见,造成东西方的对立,使西方人难以客观全面地认识西藏;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东方人重辩证思维,思考问题强调对立的交叉与和谐,西方人思考问题重对立的矛盾和斗争,致使西方人和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形成不同的“西藏观”。正是由于这种误读,导致西方人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陷阱和牢笼---西方媒体将传统西藏描绘成“香格里拉”,西方的电影、书籍、报纸等共同塑造了“香格里拉神话”(Myth of Shangri-La),西方主流媒体既受到这些神话的影响,又继续延续着这些神话,从“香格里拉神话”发展到被“香格里拉”神化,最终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Prisoners of Shangri-La)。而误导的西藏形象之所以在西方人心目中成立,是因为西方人只按照自己的现实来理解西藏,将西藏西化。西方人喜爱的“西方的”的西藏,只是他们能够从中将自己理想化的西藏形象。“百闻不如一见”,西方人只有去西藏亲眼看一看,才能了解和认识真实的西藏。西方人也只有“移情”和“换位”,摒弃“西方中心论”,以中国西藏为中心,才能真正“理解与体验”西藏,从而纠正对西藏的误读,澄清对于西藏的模糊乃至虚幻和神化了的印象。
(注:文章的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 频道周排行
- 频道T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