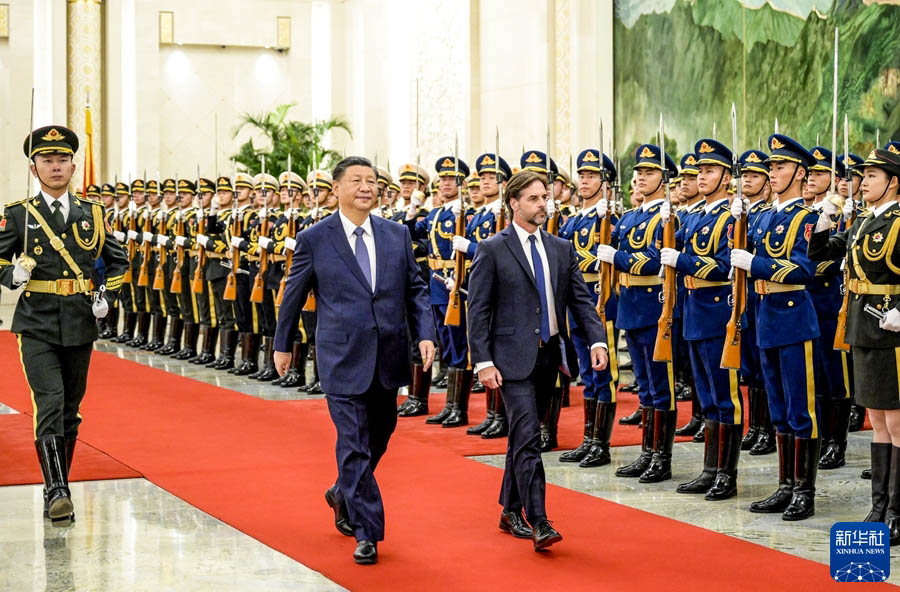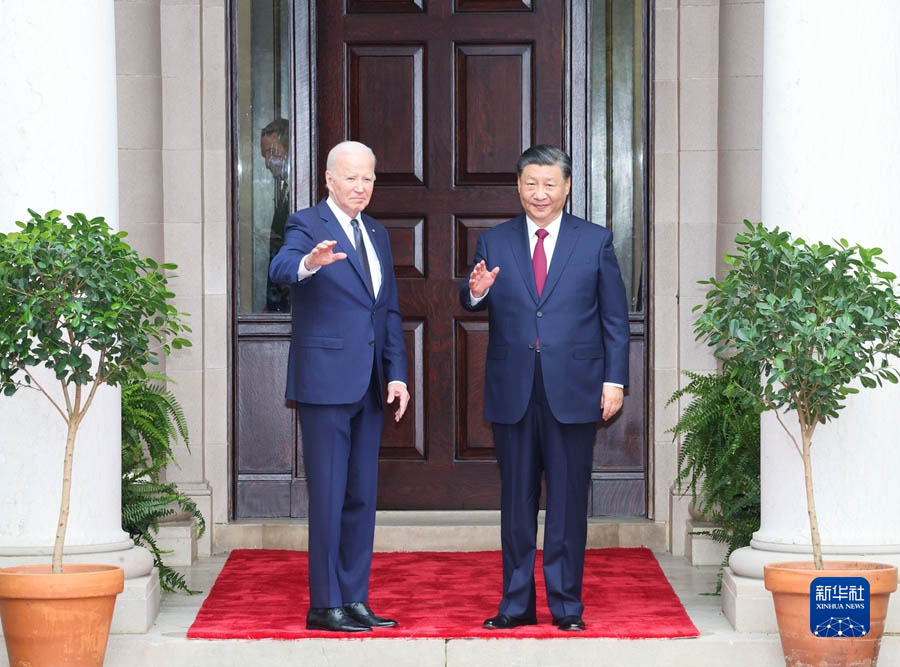【“老西藏”口述民族团结】年炘:难忘才朗班长
2020-09-14 11:53 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 点击:0

图为年炘在阅读杂志。记者 唐启胜 摄
个人简介:
年炘,男,藏族,1940年出生,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人。1950年参军入伍,1950年至1951年,奉命随军从青海进入西藏。1952年至1957年,在西藏工委日喀则分工委宣传队工作。1957年至1959年就读于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大学前身)。1960年至1963年,参与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西藏历史纪录片摄制。1965年参与筹建西藏话剧团。1985年西藏电视台成立,成为西藏第一批电视记者。2012年,年炘正式退休,现居住在成都。
我当兵时,虚岁只有十一岁,是部队最小的兵。
1950年11月,经过8个月的准备,我所在的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文艺工作队也要一起随军入藏了。我们走的是青藏线,从青海徒步走到西藏,要翻越唐古拉山。
冬天的高原气候寒冷、缺氧,再加上没有现成的道路,每个人还带有狗皮褥子、羊毛毯、小凳子等行李,一天要走上20公里山路,我们的行军极为艰苦。
从香日德镇(位于青海省都兰县)出发翻越昆仑山,我们走了二十多天。当时部队给我们每人配了一匹马,但在后面的行程中,我们几乎没人骑马。冬天大风雪天气,马也缺氧,如果马累倒了,比人死得还快。另外,人骑在马背上,双腿没法活动,血液循环不畅,容易被冻坏冻残。所以,当时骑兵部队有规定,“上山不骑马,下山牵着马”。但我是个例外,部队首长说我年纪太小了,走累了可以骑马,并嘱咐班长和副班长要好好照顾我,把我安全带下山。
最开始,对于徒步进藏我觉得很新奇,挎着小马枪,和大部队一起走,感觉可好玩了。可冬日高原的恶劣气候很快就给我当头一棒,零下30多度的天气,冻得我小腿以下完全没知觉。两三天后,兴奋劲儿一过,我就想家了,一个劲儿地哭。
我当时所在的班,班长叫才朗,是藏族同志,副班长叫星展鸿,是汉族同志,他俩轮流照顾我。我的行李,由他俩扛,我走不动路时,他俩轮流背着我走,实在背不动了,就让我骑马走一段。
天黑时,由于担心路滑摔死人,我们一般不行军,大家捡牛粪生火取暖做饭。刚开始时补给还跟得上,大家还能吃得上米、面和牛肉干,随着越来越深入高原,我们就断了补给。运气好的时候,能挖到一些野菜,但更多的时候大家是饿着肚子行军,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劳累、缺氧、饥饿不停地折磨着我们,不断有战友掉队、倒下。
到唐古拉山口时,我脑子已经完全迷糊了。有一天,班长才朗背着我走时,突然向前栽倒,狠狠地杵在地上,头上的血瞬间湿了半边脸,他的嘴唇都是黑紫的。班长摔倒后,昏迷半天才醒来,他叫来副班长,说:“这孩子是我们这儿最小的,首长吩咐一定要把他带到拉萨,后面你们一定要照看好他,这是命令!”班长又对我说:“我休息一会儿,你们先走,我稍后就赶上。”
我糊里糊涂跟着副班长就走了,翻过唐古拉山口后,有一晚露营时,我问副班长:“班长呢?他怎么还没来?”副班长这才告诉我,班长已经牺牲了。我顿时大哭起来,要不是我一直拖累班长,他怎么会出事?
班长的离开,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他牺牲时只有19岁。进出唐古拉山口的路,我后来又走了无数次。可是,才朗班长,到拉萨会合的约定,你却一辈子都没赶上!
那时候,大家没什么其他的想法,心里想着坚持,再坚持,坚持到拉萨就是胜利。到西藏后,我全身心投入西藏的发展建设中。
1960年,国家民委和解放军八一制片厂到西藏拍摄一部真实记述西藏风土人情的大型纪录片,我当翻译。这部片子共拍摄了3年,当时正是最困难的时候,但国家仍然投入巨资拍摄纪录片,充分展示了祖国对西藏的关心关爱。这部片子,到现在还放在国家民委珍藏。
1985年,西藏电视台成立后,我成了第一批电视记者。在近30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国原来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墨脱,我去过3次;在那曲海拔4800米的红旗公社采访时,我发烧40度,患上严重肺炎,差点把命丢在那儿。在阿里拍摄古格王朝遗留的壁画时,我不顾洞窟垮塌危险,一个人坚持工作了将近一周时间。
我在西藏工作超过半个世纪,我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滋养出来的文化,是它们造就了西藏灿烂独特的人文历史。回想起才朗班长他们舍生忘死进军西藏,不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西藏吗?而我拍摄的阿里皮央壁画,不正是西藏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吗?才朗班长,70年过去了,我仍然很想您!
- 频道周排行
- 频道T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