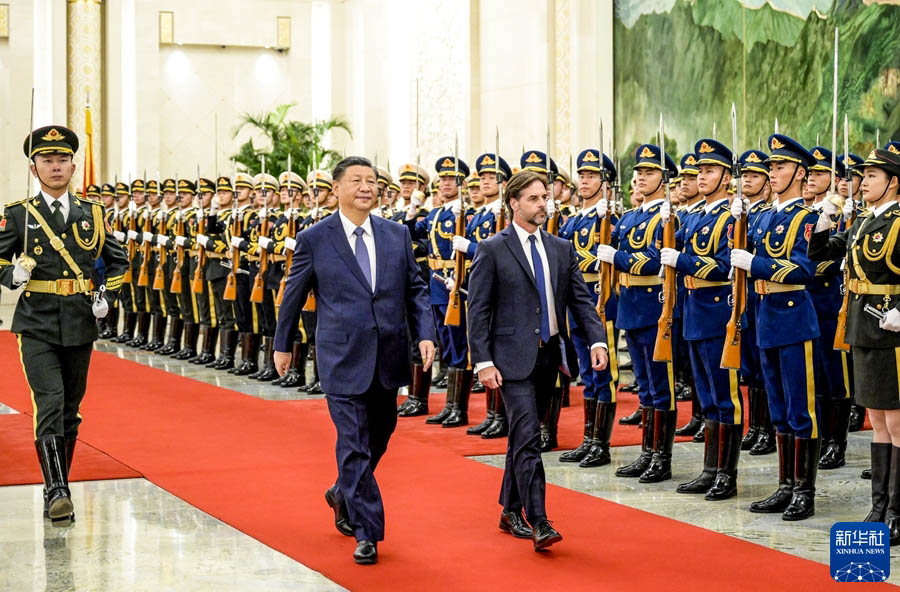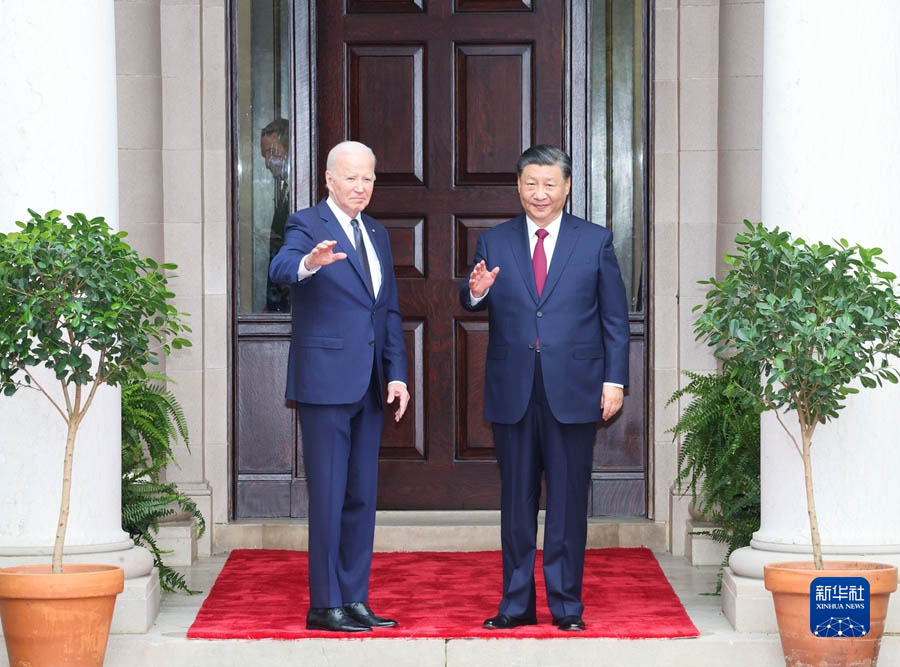陈宗烈:镜头中的西藏今昔
2014-03-13 21:45 来源:西藏新闻网 点击:0

陈宗烈用镜头记录着西藏今昔,他的心也从未离开“我们西藏”
陈宗烈在回味着,3月28日他的那些老朋友是那样高兴地度过。
今年的这一天,西藏迎来了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位在西藏工作了25年的老记者,曾经亲眼目睹农奴的悲惨生活,也见证过农奴翻身得解放时的欣悦。其中有些采访对象,成了他一生的至交。
陈宗烈是西藏民主改革初期常驻西藏的唯一摄影记者。他看到了西藏的“旧”,迎来了西藏的“新”,更用胶片记录下了西藏从“旧”到“新”的历史性进程。有论者说,陈宗烈的照片以见证者的身份,“将尘封的西藏往事之门洞开在我们眼前,历史在方寸间展现,镜头所及之处,我们的心灵也即到达。”
听77岁的陈宗烈讲西藏是一种享受:有趣闻,有轶事;有纵深,有比照。其中,他的三句口头禅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蕴含着他对西藏的炽热情感、对职业的由衷执著。
“慢慢就适应了”:困难不再是困难
身为画家张仃夫人的小姑妈,鼓励他进藏干一番事业
1956年,陈宗烈进藏,直到1980年离开,所经历的艰辛可想而知,但面对这一切,他一笑而过:“慢慢就适应了。”
小时候的陈宗烈在老家江苏丹阳过着饥不择食的生活,家庭的重担让他必须扛起长兄的责任。于是他闯荡北京,投奔小姑妈——著名画家张仃的妻子。
小姑妈很疼爱这个小侄,供他上学,之后帮他在中央新影谋得一份差事。陈宗烈很努力,1954年被组织上推荐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两年后学成回来,一纸文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当时,国家动员相关专业人员进藏工作,要求中央新影派出3名摄影师,支援刚刚创刊的《西藏日报》。陈宗烈思忖:西藏很神秘,很新鲜,去那里工作应该很有意思。而且当时西藏的摄影领域是个空白,趁年轻去打拼一下,说不定能捣鼓成点儿事。小姑妈也鼓励他报名,并承诺弟弟妹妹的生活由她来负责。
没有后顾之忧的陈宗烈带着对西藏的朦胧了解,向拉萨进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路充满了艰险与困厄;更没有想到,西藏的历史因为他的到来,变得更加形象,更加鲜活。
当年仲夏,陈宗烈怀着“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豪情,乘火车到了西宁,然后转乘汽车沿青藏公路前往拉萨。他和20多位进藏志士的“座驾”是一辆美国军用“道奇”战车——拉炮的十轮大卡。这辆车是解放战争中的战利品,车厢结构为木条加铁板,没有座位,只能坐在行李上。
“公路大部分是‘搓板路’,车上没有扶手,人和行李如同筛子里摇晃的豆粒,被颠簸得肠子都快断了。司机开车又很猛,滚滚黄尘从敞开的车尾涌入车厢,呛得人无法呼吸,只好抓起毛巾捂住嘴鼻。”陈宗烈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他们整整走了21天,才抵达拉萨。这些日子是怎样度过的?陈宗烈的回答轻描淡写:“慢慢就适应了。”
初到西藏,语言不通是个问题。怎么办?陈宗烈下定决心,“白手起家”,学!
然而,学好藏文并非易事。其口语就大有学问:贵族上层人士之间,要用敬语交谈;下层(农奴或平民)对上层人士必须用敬语;上层人士对下层讲话,或者平民之间交谈,用的是一般的藏语文口语,也就是藏语文的“普通话”。
陈宗烈刻苦学习,活学活用,“慢慢就适应了”。适应的结果是他能操着一口流利的藏语,在西藏自如地工作、生活。
除了“说”,“住”有时是个麻烦。1956年年底,陈宗烈被派往西藏黑河即现在的那曲驻站。那里海拔4700多米,10月就进入寒冬,夜间气温常在零下摄氏10度左右。刚到的那天晚上,陈宗烈没有经验,忘了生炉子取暖,结果晚上越睡越冷,再加盖被子也是冷。
第二天起床,让陈宗烈这个南方人惊呆的情景出现了:被子变得硬梆梆的,特别是紧挨着口鼻的被头,一摸,冰茬!原来他晚上呼出的水汽都没有“浪费”,发生了“物理反应”。
同一年,陈宗烈到班戈县采访挖硼砂的地质队。这里的水很苦涩,不宜饮用,必须等车辆送水来,并且每人限量供应。没有住处,就搭帐篷,但那里的风不打招呼,说刮就刮,而且一刮就是12级。大家只好挖大坑,在坑里支帐篷。放眼望去,地面上一片帐篷顶。尽管如此,陈宗烈深夜还是被冻醒了,发现自己正在露天睡,帐篷让风给“掠”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陈宗烈和地质队员一道,“慢慢就适应了”。这一“适应”,就是一个多月。
但是,陈宗烈也有无法适应的地方,特别是在民主改革前亲眼所见的农奴们的生活情景——
他曾经看到,有的农奴穿的所谓“皮袍”,不过是几张光板羊皮,缝合成一只皮筒、两只袖管。白天将“皮袍”从头顶套下,腰间系根绳子,就是衣服,内无衬衫,周身没有一缕棉纱。晚上就解开绳索,缩进皮筒,衣服就成了被子;
他曾经见到,在牧区生活的农奴有时饥寒难耐,就抓狂般四处逮牲畜。一旦成功,用铁针刺破它的动脉,靠原始的“茹毛饮血”来维持生命;
他曾经遇到,一家三兄弟共娶了一名女子,因为当时农奴主以家户为单位征收差税。如果三位兄弟选择一夫一妻制婚姻,他们的差地面积要缩小,但各自要缴纳一份差税。为了逃避盘剥,三兄弟只好共妻……
“西藏需要变革,西藏必须变革!”陈宗烈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报社流行这样一句话,‘院子里是社会主义,院子外是封建农奴社会’,我们都在期待着院子里外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们西藏……”:除了情感还是情感
韩红对他很尊敬,因为他给韩红的母亲、藏族民歌手雍西拍过照片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备受鼓舞的陈宗烈用镜头、用胶片、用内心,抒发着亲历这一过程的点滴感受。
他拍摄的《扬眉吐气》鼎鼎大名:1959年初冬,他来到拉萨达孜县汪固尔山脚下采访。当时有八个乡的农民在那里集会,他们从庄园的库房里发现了大量文契,大多是一些人身依附和高利贷债据,有的农民凑近一翻,竟然发现自己被迫按过手印的契约赫然在其间。
当时,农民们既愤怒又喜悦。愤怒源自过往的屈辱,喜悦源于现在的自由。“有人举着火把跑来将这堆文契点着了。大家欢呼起来,围在一起。有人找来棍棒,翻动着火堆,有人举手鼓掌庆贺,场面很热闹。大火焚烧的不只是一堆账本、契约,而是一个旧社会、旧制度。我赶紧找好角度,按下了快门。”多年以后,谈及这幅凝固西藏历史印迹的照片,陈宗烈依然流露出一份得意。
他拍摄了一系列讴歌西藏变革的照片:《丰收的喜悦》《歌唱新生活》《分牲畜》……这些名字就透露出一股迎来新时代的欢悦。陈宗烈足迹遍布除阿里(1978年前阿里地区由新疆代管)以外的整个西藏,所到之处,他都记录下那里的变革潮涌、风土人情。
陈宗烈把西藏变迁瞬间定格,西藏在他的心目中也渐渐变得明朗而清晰。尽管已经离开这片热土将近30年,尽管在藏多年让他患上了肺气肿,但一谈及西藏,他不停地说着“我们西藏如何如何”,喜上眉梢、乐在其中。
从不适应到适应,陈宗烈发现“我们西藏”的食物太有味道了。刚回北京时,喝不上酥油茶,浑身不对劲。他就往军用水壶里装茶水、盐巴和奶油,自制起酥油茶来。“尽管风味上有些欠缺,但可以解馋”。
后来,北京有了藏餐厅,陈宗烈来了精神,经常光顾。比如他喜欢到歌手韩红开的藏餐厅坐坐。韩红对他很尊敬,因为他给韩红的母亲、藏族民歌手雍西拍过照片。
现在,去陈宗烈家里,他会热情欢迎你的到来。进门了,他认真地献上洁白的哈达,因为这是“我们西藏”的风俗。
尽管是摄影记者,陈宗烈的文字也很见功力。在一本著作里,他这样描述在“我们西藏”常见的朝拜情形:“(大昭寺)门前青石铺地,每天有许多信徒到此匍匐跪拜。他们脱靴赤足,面朝大门,双手合十,举手过头、至脸、再至胸,向前方注目三拜,口中不断祈祷,然后双膝跪下,五体投地,额头向石板地面叩去,咚咚作响。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对佛最虔诚的礼拜。”
藏历新年是“我们西藏”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陈宗烈对曾经到藏族同事家过藏历新年的情景记忆犹新。
藏历新年的年夜饭主食是“古突”,由九种原料加工而成的面疙瘩。“古突”有各式各样的“馅”,如象征意志坚强的干净小石粒,象征泼辣直爽的辣椒,象征温柔的羊毛,象征纯洁的小瓷片。另外,还会捏些小面人一道下锅,活脱脱一个藏式“乱炖”。
煮熟了,大家各自用碗来盛“古突”,然后小心翼翼地进食。按照传统,吃到小面人的,不管是长幼尊卑,都要学狗吠、学驴叫。
“我很幸运,碗中的‘古突’里,有一小块瓷片。藏族同胞们都向我道喜,说来年我将吉星高照。”回忆起这段趣事,陈宗烈像孩子一样笑得很开心。
陈宗烈最喜欢的茶是酥油茶,最喜欢的酒是青稞酒,最喜欢的风景在林芝地区的察隅县,“那里跟童话描述的一个模样,整座山全是玫瑰……春天的时候,满山的野桃花刚开过,没几天就轮到杜鹃花‘上岗’了。也就是说,今天是一山的桃花,过几天又成了一山的杜鹃花……”谈及西藏的美景,陈宗烈陶醉其中,意犹未尽。
不管是茶,是酒,还是景,在陈宗烈那里,都留着“我们西藏”的味道。他成家在西藏,孩子生在西藏。1980年他被调回北京,在北京周报历任记者、组长、编委,但他的内心不曾离开西藏,至今编著了多部关于“我们西藏”的图书,并乐此不疲,有求必应。1987年和1990年他两次重返西藏,访故地,察变化,会友朋,“回家的感觉真好”。
“我这里有故事……”:故事不只是故事
由于和狼生死对峙过,所以至今他不相信什么“与狼共舞”
“第一次听陈宗烈讲西藏的故事,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我也算是个‘老西藏’,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西藏工作过8年,可是相比有25年‘藏龄’的陈宗烈先生,那只是小巫见大巫”,《中国西藏》杂志社社长张晓明说。
陈宗烈对西藏如数家珍。他的同事、北京周报摄影记者徐向军有次要前往西藏采访,陈宗烈给他提供了一大堆采访线索,“简直就是张活地图”。后来,徐向军发现打着他的“旗号”可以获得很多的采访便利,“在西藏,他似乎成了通行证”。
现在,提到“我们西藏”的一点什么事,陈宗烈总是有故事候着,等你“上钩”。
你说布达拉宫很漂亮很雄伟,陈宗烈会说:“噢,你知道吗?日喀则有个小布达拉宫,我这里有故事……”
原来,相传当年后藏领袖仰慕壮丽的布达拉宫,打算仿造一座,但苦于无法掌握布达拉宫的建设规划,就派人到拉萨去索要,前藏官员自然是“天机不可泄露”。来者急中生智,就找个萝卜,对照布达拉宫的形状雕刻了个模型,喜洋洋地回去“领赏”了。工匠如获至宝,捧着这个萝卜动工了。结果事与愿违,跟布达拉宫相比差距不小。原因颇具戏剧性:由于高原气候干燥,加上路途遥远,萝卜模型干瘪了,变了形。
你说你到过拉孜县,陈宗烈会说:“嘿嘿,我这里有故事,拉孜有一座铁索桥。这桥不简单,跟藏戏的起源有关……”
原来,公元14世纪,僧人唐东杰布才华出众,四处云游。他发现西藏各地没有桥梁,百姓过河又吃力又危险。他决心要为民造福,于是刻苦试验,发明了建造铁索桥的技术。但他只是个穷喇嘛,无钱无权,计划只能搁浅。
后来,他化缘时结识一位施主,家中有七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女儿。唐东杰布计上心头,就说服施主和这七姐妹,并吸收几个年轻小伙儿,组成了西藏历史上首个歌舞演出团体。这可是个新鲜玩意儿,一演出广受欢迎,募集到了大量的“演出费”。“老板”唐东杰布用这笔钱款修了几座铁索桥,拉孜的这座就是其中之一。为此,唐东杰布被人们尊奉为藏戏祖师。
关于西藏的故事,陈宗烈有一箩筐。除了这样的掌故,还有他亲历的一些险境,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位记者为了实践记录历史的责任,需要全身心的付出,有时甚至是生命。
有一次,陈宗烈随工作队下乡采访。在途中休整时,他发现牧场周围冒着气体,原来附近有温泉群。这可有“货”了,陈宗烈拿着相机就跑,不顾这里海拔4800多米。来到一处卵石堆旁,一个浅井似的石坑就像一口开水锅,泥浆水在坑中“咕嘟、咕嘟”翻腾作响。陈宗烈正想举起相机“咔嚓”,突然感觉身子往下沉,脚踩的石头在陷塌,右脚滑进了沸泉,滚烫的水把他的靴子灌了个“饱”。
“幸好身边有同志奋力相救,把我拉了出来。也幸好我那天穿着长统马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后来有人拿几个鸡蛋放进沸泉里,不到三分钟就煮熟了。大家帮我把靴子脱下来,右脚上全是水泡,养了一个多月才好转”,陈宗烈说。
1957年,陈宗烈到安多县采访,独自在高原上策马前行。走着走着,马突然不动了,还往后缩。怎么回事?陈宗烈一抬头,前方有几只狗形动物依次排开。是野狗吗?难道马儿这么胆小,连狗也怕?
耳边传来的叫声让陈宗烈顿时懵了:是狼!野狼!那“嗷嗷”的叫声凄厉而恐怖。
事态突然,陈宗烈才想起腰间别着一把枪。这是当时为了外出安全,组织上给他派发的。他扣动扳机,向狼群连射子弹。马儿更受惊吓,原地乱跳,嘶鸣不已。狼群一愣,停住了脚步。但它们是“老江湖”了,或许认定一人一马一枪,它们“弟兄”几个不在话下,于是稍事“整顿”,结队奔袭而来。
怎么办?就这样“束手被擒”?“我已经看到了狼的毛脸,咧开的大嘴和雪白的牙齿,刹那间,我脑里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一次次扣动扳机……”幸好,枪声引起在附近放牧的藏族同胞的警觉,他们赶了过来,投掷石块,将“领头狼”击中在地。其他的野狼见势不妙,纷纷落荒而逃。
脱险后,陈宗烈随即翻身下马,向三位救命的牧民再三道谢。“至今我都不相信‘与狼共舞’的故事,那太过离谱了”。到现在,陈宗烈还心有余悸。
一肚子西藏故事的陈宗烈本身就是一个故事,留待人们慢慢地去诉说。
(责编:晶晶)
- 频道周排行
- 频道T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