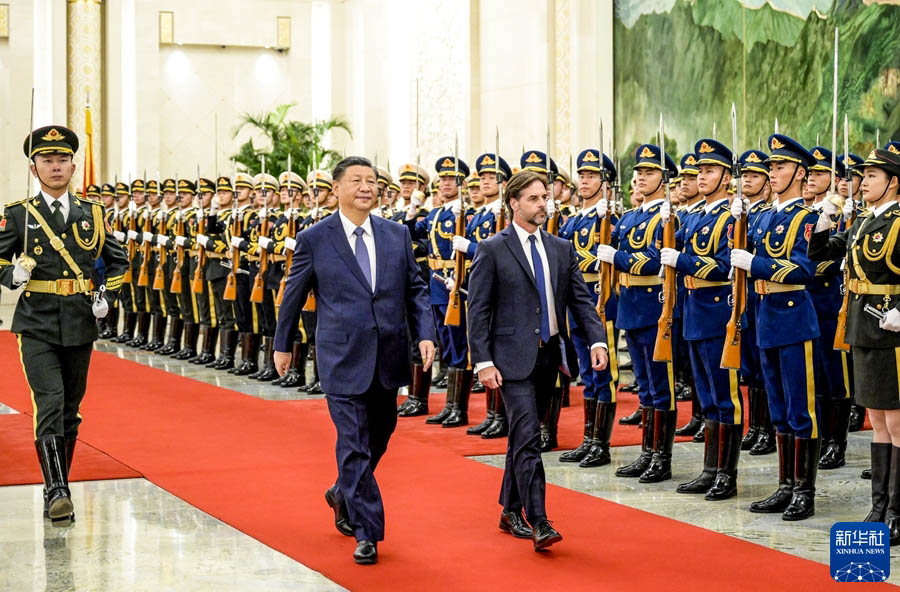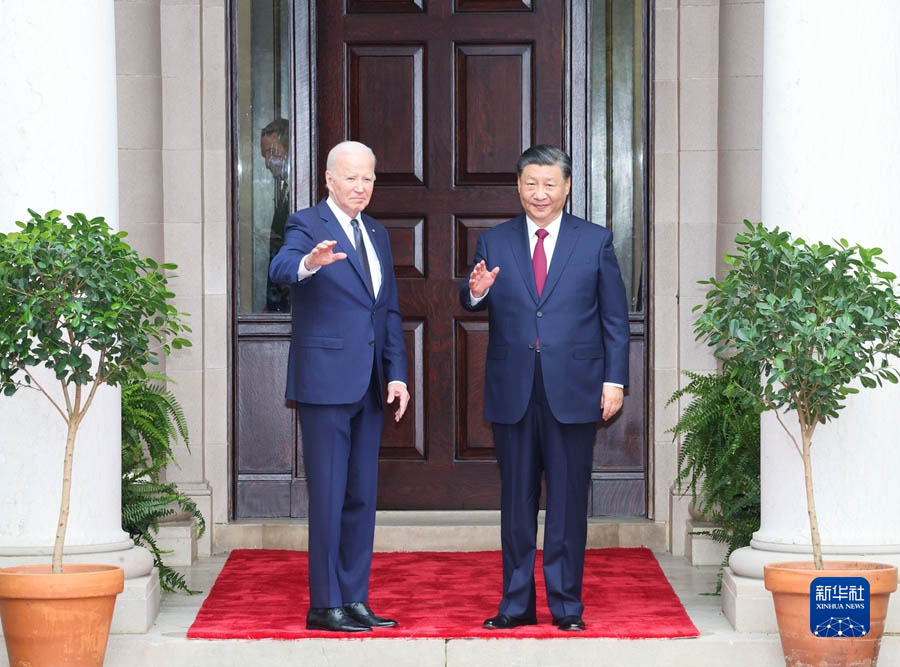瞭望新闻周刊:西藏春天的面孔
2014-03-13 21:44 来源:西藏新闻网 点击:0
|
在这传统与现代的叠影里,在这神圣与世俗的交织处,可以看到西藏的“真身” 傍晚七点多钟,春日余晖透过拉萨玛吉阿米餐吧的窗户暖暖地照到脸上。面前,一保温壶藏式甜茶,一碗甜甜酸酸的“扎西德勒”。旁边,一位头发烫得微曲、染成黄色的年轻女子,和她抱着相机的男伴,放下行囊,翻看着写满现代爱情故事的藏纸留言本。 时值淡季,店里的人不到十个。本刊记者看到,一窗之隔,八廓街上人流依然密密麻麻——右手转经、左手数珠、口中喃喃、神色虔诚、顺时针缓缓移动的信徒,拄着拐杖、弯腰九十度、盯着地面怕踩着微小生灵的老人,神情惬意地散步、新奇地东张西望、有的还逆向而行的游客,展示民族工艺品、小声吆喝拉客的小摊贩,下班、放学回家的当地居民…… 拉萨八廓街东南角的玛吉阿米餐吧,曾留下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动人故事。窗内窗外,阳光照射着古老又现代的西藏。 那些人来了,又回去了;这些人扎根在此,有的也走出去。不甘迫于生活的人们,来此追问生命;追问生命的人们,也返身生活。人群日复一日的流动中,千年大昭寺的金顶光辉宁静,藏地蓝天澄澈辽廓,时而漂起的云朵,是它的拈花一笑。 在这传统与现代的叠影里,在这神圣与世俗的交织处,在这安宁与喧嚣的融合境,一束阳光,照亮西藏千百年的变与不变,映射出人间沧桑,清澈如镜。 “藏漂”的舍与不舍 白西装,黑毛衣,绣花长裤,绣花鞋。在充满各色人等的“藏漂”中,衣着时尚的羽芊并不特别显眼。 十年前,汉藏混血的羽芊到拉萨探亲,对这个城市“一见钟情”,在这120万平方公里的神奇土地上“漂”了起来。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内地青年像候鸟一样不定期地漂在拉萨,一些匆匆过客灵感迸发,其中一位还画出《西藏组画》,出了名,他叫陈丹青。 本地人告诉本刊记者,“藏漂”流动性很大,每年在二三百人。他们中有些人干脆放弃从前的生活,在此享受自由而轻松的生活。与寻找成功机会的“北漂”不同,“藏漂”们自认是“精神上的漂泊”。 自身即是藏漂一员的羽芊曾深入了解过藏漂们。她把藏漂分为几类:对内地都市节奏快、压力大的生活方式心生厌倦,或在情感生活中受到伤害的人们,试图在西藏这方净土得到慰藉,疗治精神伤口;受到西藏独特文化吸引的自由艺术家,以西藏的自然景观、宗教历史、民间风情作为创作的资源和灵感;有钱而有闲的旅行家——“驴友”,定期聚在一起到西藏探险观光。 一位外号叫“鸡毛”的藏漂,在内地一家规模很大的外资企业做空调维修工程师,每天衣冠楚楚,受人羡慕。而漂在拉萨的几个月里,他整日身着铠甲,头戴锦鸡羽毛,身背弓箭,骑一辆修饰得很另类的自行车在街上游荡,俨然是愤世嫉俗的行为艺术家。 央金玛酒吧的老板、新疆姑娘丹丹也曾是藏漂。2007年第一次到拉萨,一下就喜欢上了这儿的一切: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文化深厚,生活节奏缓慢。几个月前,她盘下一个小酒吧,维持基本生活,而多数时间在街上晒太阳、闲逛。 矮房子酒吧老板、东北小伙吴彪则自认没那么浪漫。他说在这里开酒吧就是为了赚钱,“西藏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没感觉,其实这里什么都没有。”但2002年第一次到西藏旅游后,“一回家就想回到这里来。”他不想酒吧里鱼龙混杂,故意把酒水卖得很贵,没人的时候就独自喝美国百威,听印度音乐。 西藏给藏漂们逃离压力和焦虑的选择,提供相对封闭、自成一体的独特环境。既不能过分功利,又要有一定便利,藏漂们绝大多数选择了西藏最大的城市——拉萨。 想逃离现代,又离不开现代。“藏漂”们的舍与不舍,是现代人对生存的追问。 “神鹰”与“天路” 面对现代,西藏人有自己的经历与眼睛。 日喀则市31岁的农民达瓦平措家住日亚公路旁,他对本刊记者说,当年父亲进城牵着毛驴,走着土路去,现在他进城,开着手扶拖拉机,走的是柏油路。他现在最想把土房变成石木结构,就像村里先富起来的人们一样。 上世纪90年代,一首《向往神鹰》曾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歌词作者扎西达娃对现代文明有着的西藏式的浪漫表述: 在每一天太阳升起的地方, 银色的神鹰来到了古老的地方。 雪域之外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 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 祖先们一生也没有越完的路, 啊,神鹰—— 转眼就改变了大地的模样。 …… 这首歌是写给第一代藏族飞行员扎西泽仁的。出生于农奴之家的扎西泽仁说,“我能健康地成长,并能成为一名飞行员,完全是因为我赶上了好时代。” 在西藏,藏族把飞机称为他们恭敬的“神鹰”,把青藏铁路称为“吉祥天路”。 “西藏人的生活要进步,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拉萨市边上塔马村支书格桑卓嘎日前在随团访问加拿大时说,“如果我们的父母想让社会一直保持不变,我们不会同意。就如同我们现在如果不让社会继续发展,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同意。” 对“现代”,西藏最早感受到其凶狠残忍的一面。19世纪前后,英国人屡次入侵西藏。1904年4月,英国人侵入西藏占领江孜。江孜军民紧急动员起16000人,凭借原始的大刀、长矛、梭标、弓箭,对抗英军新式火器,死守宗山城堡。8个月后,藏军弹尽粮绝,守卫者跳崖牺牲。如今宗山城堡的断壁残垣中,还能看到英军火枪的累累弹痕。 这个命运与当年广大中国内地相同。 而享受到现代化的便利,也一样在祖国稳定强盛之后。 西藏需要现代化,谁反对发展,“让他去拉萨河边三天三夜吃风喝屁,看他干不干?”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党委书记孙勇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 “香格里拉囚徒” 入侵西藏的西方殖民者,如今成为“香格里拉囚徒”,无法自拔。 1933年,工业文明受挫的大萧条时代,美籍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出版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在西方人心中种下“香格里拉”情结:远离尘嚣的人间仙境,神秘浪漫的世外桃源,带着东方主义色彩的幻象,直到现代金融文明受到讽刺性打击的今天,仍然挥之不去。 旧西藏不是从未到过西藏的希尔顿想象中的“香格里拉”。一位最早进入西藏的解放军战士回忆,“农奴们对主人与喇嘛,都非常害怕,那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恐惧,他们说话时,甚至都不敢抬头去看他们的脸,生怕他们一不高兴,惹来滔天大祸。” 95%以上的人生活在日日夜夜的恐惧中,这样的地方难以被称为“人间仙境”。 民主改革后,广大农奴获得了土地和自由,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他们感谢新生活,把解放军叫“金珠玛米”,菩萨兵;把毛主席看成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的化身。直到今天,许多农奴后代家中的佛堂上,供着佛像、菩萨像、宗教领袖像,还有毛主席像。 就在此时,向往香格里拉的西方人把对西藏的美化,一转而变为对西藏的丑化,持续了50年。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等对本刊记者说,西方人误读西藏,有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东方人重辩证思维,思考问题强调对立的交叉与和谐,西方人思考问题重对立的矛盾和斗争。但这个误读更是由于情感上的距离和政治上的偏见,他们的有意误读,是不认可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 一些西方人因此陷入困境无法自拔——西方媒体将传统西藏描绘成“香格里拉”,西方的电影、书籍、报纸等共同塑造了“香格里拉神话”,从“香格里拉神话”发展到被“香格里拉”神化。 固执于矛盾和斗争的西式现代化,无法存活于西藏;固执于自己好恶的标尺,拒绝现实,也一定会成为囚徒,不管是哪一种。 传统与现代的叠影 西藏,如今是一幅传统与现代并存融合的图景:八廓街上,有卖给游人的唐卡、卡垫、藏刀、转经筒,也有内地的种种日常生活用品。日喀则农宅中,一边是供着佛像和班禅像的经堂,另一边是摆着进口大彩电的客厅,厨房里,一边是烧牛粪饼的火炉,一边是煤气罐和沼气炉。哲蚌寺和扎什伦布寺等寺庙里,酥油灯和吊顶电灯上下辉映…… 传统从来不是变动不居的。从来自普陀山的猕猴传说,到苯教的创立与雅隆悉补野部落的崛起,再到吐蕃王朝的兴盛与大唐、南亚佛教的传入,又经政教合一并纳入元明清版图。尽管雪域高原相对封闭,但其内部的发展及与外部的交流从未停歇,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其自身也是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心胸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底蕴。拉萨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大昭寺,便融合了藏、唐、尼泊尔、印度的建筑风格,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现代化事物进入西藏,是时代进程的一个部分。而在保护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上,西藏走在前列。 比如西藏的寺庙,对外来游客要收几十上百元的门票,旺季时还限制人数与时间,而对朝佛的藏族群众或不收分毫,或仅象征性地收取一两元钱。西藏的天葬习俗,也通过相关法规予以尊重和保留。 扎什伦布寺一位年轻僧人颇有兴致地讲起,在全国遭难的“文革”时期,中央领导特意把布达拉宫和几大寺改为国家粮库,红卫兵和造反群众就不敢冲击了。 近二三十年对拉萨旧城的改造也是保护传统的一个范例。在以大昭寺为“心”、八廓街为“脉”方圆一平方公里多的老城区,依“修旧如旧、保持原貌”原则,在完成道路、水电改造后及建筑物内部的结构的部分改变后,典型的藏族建筑精髓和藏族生活传统被完整保存着。 活生生的传统才具有现代价值。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李作言向本刊记者介绍,日喀则已举办七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珠峰东南侧定结县陈搪乡的夏尔巴人是这个节日的明星。他们每次都会提前三四个月排练,一到节日,先步行五六个小时,再开十多个小时拖拉机来到市区,在扎什伦布寺前广场布置的现代化舞台上表演他们的原生态歌舞,“纯美、朴素,有种原始的和谐的味道”李作言说。 神圣难以被染污 传统与现代相叠的背后,是神圣与世俗的交织。藏传佛教是西藏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部分,渗透于西藏的一切时、一切处。西藏的神圣一面,和光同尘,未曾改变。 一千三百多年前,当大唐和尼泊尔的两位公主带着佛像来到拉萨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待布达拉宫与大昭寺拔地而起后,神圣与世俗的权力一并确立,这个海拔3600多米的相对低地成为雪域高原人们心目的“最高峰”。 后来的朗达玛灭佛与吐蕃王朝的崩溃,也是宗教冲突与世俗之战相混。随后数百年,拉萨几乎成为被遗忘的边陲小城。直至1409年,宗喀巴的传昭法会使这里再次成为信徒们“神圣之城”,政教合一的逐渐强化亦使得它成为世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1936年,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在《圣城拉萨》中记载说,这座围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小城,聚集着僧侣、信徒、贵族、乞丐,充满市民气息,同样有着某种庄严的神圣:“当一缕阳光在布达拉宫金色屋顶上闪烁时,会让你激动不已。” 神圣与世俗的交织,源于人的灵魂与身体的二重性,对精神家园与物质家园的双重追求。近几十年,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物欲与身体欲泛滥,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为无法满足的欲望陷阱,丧失了幸福的感受。这些年,为重寻精神家园,内地上下已付出更多努力。 这正是“藏漂”们内心难以言说的愿望。在他们眼中这块精神与生态的“净土”,是不可多得的心灵栖息之地,“回到拉萨”,是藏民游子的呼声,也是这些外来者的心声。 西藏的神圣难以被染污。哲蚌寺寺管会常务副主任阿旺群增对本刊记者说,从上世纪80年代十世班禅大师提出“以寺养寺”以来,寺庙兴办农场、公司有了收入,信徒的供奉、布施也多了。现在学经班的僧人可以一心一意,不必像过去一样为生活来源操心。他作为“干活的”,每半年可发五千多元工资,现在用的手机就是花三千多元从成都买来的,与内外联系很方便。 很多农村藏民说,现在条件好了,去寺庙的道路更通畅,家里的经堂也更完备,他们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宗教活动。当然年轻一代也有不少忙于工作、奔前程,与父辈的活动渐行渐远,“这是他们的自由,只要不做坏事就行。”格桑次仁说。 受访的中国的藏学家们认为,今天“现代化的观念正在深入到大部分藏传佛教信仰者的心中,而且支持藏传佛教在某些方面改革和向现代转换的人也很多。” 林芝农业技术员次仁卓玛有一次去教当地村民杀虫,很多百姓守持佛教“不杀生”的戒律,不愿用他们称为“毒水”的农药。 “后来有些人去问活佛,活佛告诉他们,为了保护庄稼而杀害虫没错。”次仁卓玛说,村民们这才愿意使用农药,但在打药之前,还是要先焚烧松柏树枝,这是他们和神对话的一种仪式。 “西藏经验”可期 本刊记者在藏地多个农村接触到的农民,生活条件较好的会讲如何积善行德,而贫困的多希望改善生活,如修个新房,买个拖拉机。 西藏,似乎更有条件享受现代化的利益,而避免其有害的一面。 在西藏普通民众中,“现代性问题,如人对自身命运的不确定性、对他人、对环境的焦虑感,还没有出现。”从上海来到西藏两年后,李作言作了如是结论。 他认为,此处独特的精神信仰氛围与生态环境,决定了出现现代性焦虑的可能性不大,生态并不全然指净土,还包括较恶劣的生存环境,“氧气都上不来时,你还想这想那?” “即使有焦虑,他们化解的方式也比较多”,逛林卡、唱歌跳舞、呼朋唤友一起喝酒等,是藏民的生活常态。 在西藏工作生活38年的孙勇认为,藏民的“真善美程度较高”。 有一年下乡,一位十六七岁的藏族姑娘挡在公路上向孙勇他们招手,他们还以为她家里出了事,下车一问,姑娘有些羞涩地讲,“家里刚做了新鲜酸奶,你们要不要去吃?”后来知道,家里只有她和妹妹两人,父母放牧去了,“她们心中没有‘坏人’的概念。”孙勇很感慨。 人间天国难得,心中净土可求。清洗贪嗔痴,人心干净,天地才会干净。人心和谐,世界才能和谐。 北京大学教授叶朗说,中华文化中大可开掘出人类社会共同的普适价值。同样,藏学专家们也认为,作为中华文化中独特的一支,西藏文化也有可启示全中国、全世界的价值所在,不是只作为一种对边缘事物的猎奇性消费。 今年“3·28”50周年大庆时,西藏宣布其新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同全国一道实现现代化。孙勇说,西藏起步虽晚,但有些方面比内地一些省还好,如对传统和生态的保护,西藏的后发也正是其优势所在,甚至可提供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西藏经验”。(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尕玛多吉 刘江 胡星 颜园园)
(责编:晶晶) |
- 频道周排行
- 频道T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