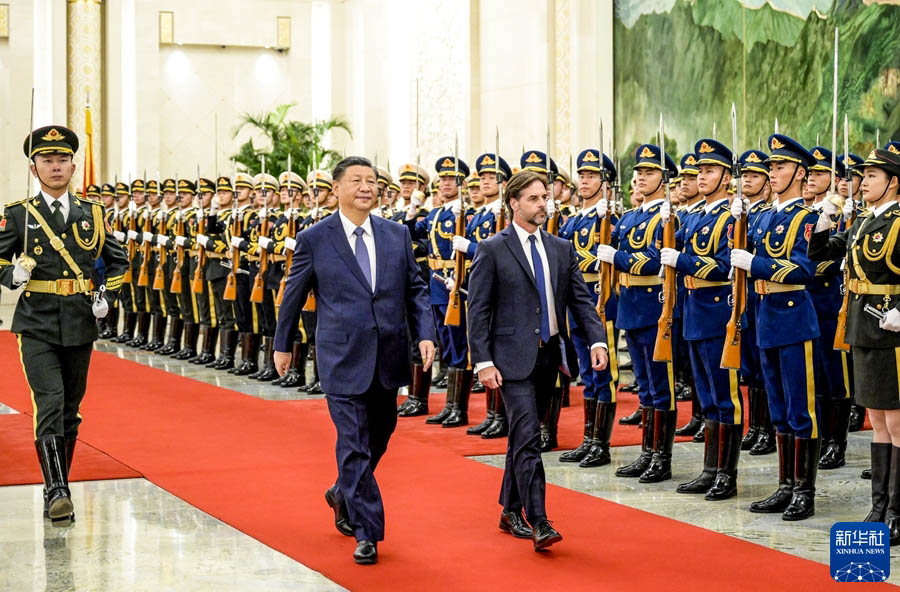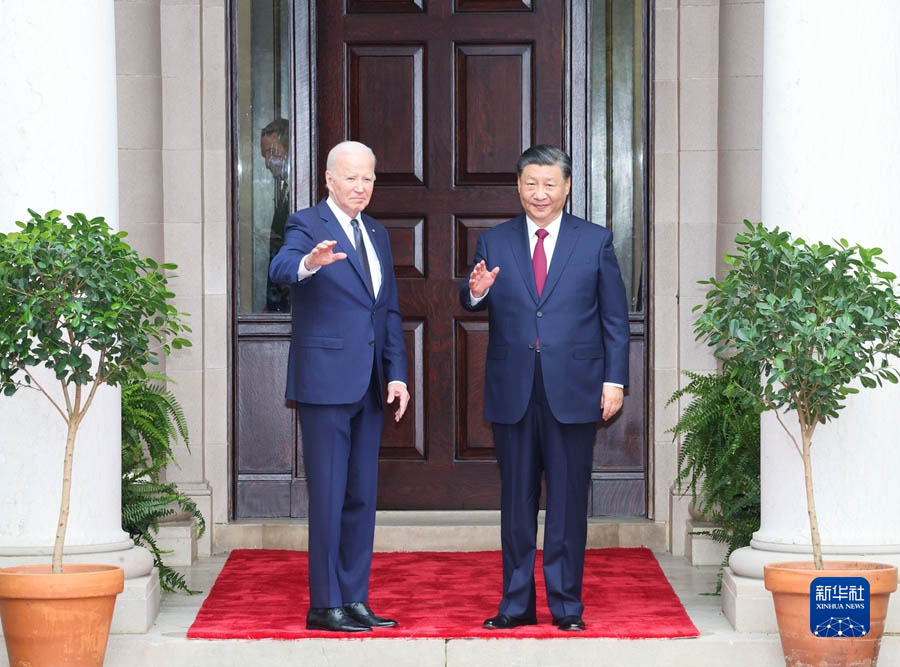“我把青春献给了西藏”——访18军老战士徐永亮
2014-03-13 21:23 来源:西藏新闻网 点击:0

8月11日,徐永亮在家中接受本网专访。 新华网 黄锐 摄
新华网北京8月18日电 题:“我把青春献给了西藏”——访18军老战士徐永亮
王春华 冯文雅 黄锐
“世界上如果有灵魂的话,我的灵魂已经留在西藏了。”原18军老战士、原西藏军区话剧团副团长徐永亮注视着我们说,眼中熠熠闪光。
徐永亮16岁进藏,在西藏度过了“生最重要的20年”。离藏近40年来,由于身体的原因难返“故园”,徐永亮一直打探着一切和西藏有关的消息,读相关的书,了解相关的事。西藏那段“难以割舍”的青春岁月,成了他数十年来最美好的回忆。
雪域圣地一路歌
徐永亮说,当时他们只是抱着“驱逐帝国主义,解放祖国最后一块国土”的一腔热血,实际上“对西藏的情况一无所知”。他笑着补充道,正是军长张国华,才让他们这些文艺兵有机会踏上西藏那片土地。
当年进军西藏的命令下达后,西南军区邓小平政委指示“要轻装前进”,文工队被减了下来。在红军时期曾做过宣传工作的18军军长张国华,深知文艺的作用,向当时西南军区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坚决要求“带文工队进藏”,称要在西藏开展工作就必须先通过文艺和文化这条战线。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徐永亮所在18军54师文工队被整队调到了军文工团。
进藏部队抵达拉萨举行入城式时,不少藏族同胞第一次见到解放军、第一次见到红旗、军乐队、腰鼓队和秧歌队,“拉萨群众全城出动来看解放军”。不过还是有一些捣乱分子从房上扔飞石,还往解放军身上吐吐沫,一些“坏家伙”会突然用身体撞人,当地人称之为“扛膀子”。
“人家砸你,只要还没被打趴下,就要接着表演。”徐永亮说,“那时候我们有一条规定,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刚到西藏时,由于语言还不通,文工团通过演出“与藏族同胞拉近感情”,演员们穿上彩妆,打起腰鼓,围着村庄转。老百姓一看,解放军在唱戏,就过来了。文工团开始演出宣传十七条协议,那时都有藏文翻译。
“说实在的,藏族老百姓就是通过文艺演出认识解放军的,又是通过解放军的宣传和模范作用,认识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徐永亮强调说,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宛若乐队指挥。

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抵达拉萨后,受到藏族各界的热烈欢迎(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那时候给西藏贵族演出也是文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徐永亮说,“文工团那时每周得有一天去陪贵族们跳舞。”贵族小姐“一个个长得挺漂亮的”,留过学,会说英语。他们的生活非常奢侈,“吃高级奶粉、巧克力”;很洋气,“还抹着香水”。
徐永亮还给我们讲述了文工团为达赖演出的一些往事。
部队刚到拉萨时,达赖在罗布林卡第一次接见了进藏部队团以上干部,第一句话就是:“汉官,你们辛苦了。”随后就要请大家吃饭。按照当时西藏上层社会的规定,宴会必定有歌舞伴随。文工团许多女兵纷纷表示不满:“我们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怎么能做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呢”,不愿意赴宴。军区首长谭冠三知道后,亲自来做工作,强调在宴会上演出“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大家才应邀前去演出。
文工团第二次为达赖演出时逢藏历年,按照藏传佛教传统,不允许女性进入布达拉宫。经过交涉,文工团的汉族女演员获准进入。当时他们跳的是苏联红军舞、新疆舞,还有《孔雀吃水》的藏区舞蹈。
徐永亮说,达赖观看表演在楼上,他面前挡着一个黄纱。看着看着,一高兴就把黄纱扯下了,拿出相机拍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达赖,达赖喇嘛那时还是一个小孩。”

文工团表演《新米节》的小歌剧。(徐永亮供图,8月11日翻拍)
还有一次,文工团表演一个表现军民关系的小歌剧《新米节》,演完之后徐永亮他们正在后台卸妆,团长走进来说:“停下来,不要卸,达赖还要再看我们演一遍。”“我当时就对我们那女主角开玩笑说,‘都怪你太漂亮了,’后来,我们就又给他演了一遍。”
“达赖最佩服的就是毛主席了。”徐永亮说,“1954年达赖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毛主席接见了他。毛主席说,‘西藏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喇嘛制度的问题,你们的宗教信仰我不管,但社会科学的进步这点你们一定要接受,社会要进步啊。’”
说到这里,徐永亮看着我们,感慨地说:“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在西藏、乃至在世界上都是创举。”
当年在西藏,上级要求文工团要有“军队的气魄,有民族的风格”。因而,徐永亮和他的战友们还向西藏文化学习。
1953年开始,文工团专门请民间最好的艺人来教藏族舞蹈,还向民间艺人学唱藏戏,学的第一部藏戏是八大藏戏之一的《苏吉尼玛》。徐永亮说,文工团有位歌唱演员叫黄崇德,“艺术感觉特别好”,她的藏戏演唱水平一些西藏贵族看了都赞不绝口。

8月11日,徐永亮给本网编辑演唱他在西藏学的民歌。 新华网 黄锐 摄
徐永亮1954年曾在太昭(现更名为工布江达)带民工修路。民工们特别爱唱歌,那些民歌调子也特别好听。徐永亮就请人用藏文记了下来。现场他还给我们唱了一首,歌词是:“解放军到西藏,幸福生活有保障,修公路呀,修到自己的家乡……”当时的西藏贵族索康担忧地说:“坏了,公路修通了,我们虽然收了解放军千百万个大洋,但我们失去了千百万个奴隶。”
文工团在向藏文化学习的过程中,也丰富了自己、陶冶了自己,对后来的一些创作也有很大帮助,著名的《洗衣歌》就是这么创作出来的。
“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过程中,文艺工作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徐永亮激动地说,“正是通过文艺,才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传到了西藏。事实也说明了‘扩大文艺队伍,加强这条战线’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决策。”
风雪高原苦与乐
13岁入伍时,徐永亮还是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到部队后他养成了自学的“坏习惯”——每晚在肚皮上默写生字,这个习惯还用到了藏语学习上,一直带到了西藏,等他结婚后“划”字划到了爱人的手上,把爱人吓到了,从那儿之后他的习惯才慢慢改掉。徐永亮说,学藏语是中央进藏部队的基本要求之一。尽管进藏路上大家都在坚持学习,但他们第一次在用藏语演出时,还是“藏族听了像是在说汉语,汉族听了又像是在说藏语”。

8月11日,徐永亮向本网编辑讲述进军西藏时过雪山的情景。 新华网 黄锐 摄
1951年7月1日部队由甘孜到拉萨进发,行程近千公里,一路单靠两条腿走路,偶尔还会被驮给养的“生荒马”咬。伴着军歌嘹亮,部队一路爬雪山、过冰河。行军路上,从将军到士兵一边忍耐着“世界上无法克服的困难——缺氧”,一边坚持学藏语、学文化,了解藏族民俗和体验藏民生活。有时练习喝酥油练到呕吐,文艺兵们开玩笑说,这样演节目就“更有藏味了”。
提起部队渡金沙江的那段历史,徐永亮给我们讲了一段趣事。渡江没有渡船,只有藏族的牛皮船,船身是用牛皮缝的,缝好后用棍子支起来,下水后就像个“碗”在江里漂着,一只船只能坐四、五个人。那时有一个老同志诗性大发,刚写了第一句“牛皮船好像大花碗”,突然有人喊去赶马,他就放下日记本,回来后一看,多了一句“我们好比稀饭”,听者大笑,这时,又有人追了一句“船夫从这边把我们舀到那边”。

资料图片:演员在表演舞蹈《牛皮船》(2009年5月1日摄)。 当晚,由西藏文化厅和西藏珠穆朗玛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大型唐卡式歌舞诗《幸福在路上》在拉萨进行了首次商业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看,为逐步升温的西藏旅游市场又增添了一抹亮色。 新华社记者 涂洪长 摄
在艰难的行军途中,文艺兵们一边行军,一边还要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给战士们鼓劲儿。他们把雪山当舞台,以蓝天为大幕,在沿途地势最险要的地方搭起了“鼓动棚”。每当部队经过高山,他们都要先于几个小时爬上山顶,在山顶设上茶水站,快板组,唱歌队,鼓舞着部队爬过雪山。
过丹达山时,他们在山顶又跳舞又唱歌,由于缺氧,有的女演员眼看着嘴唇发紫。那时候三个月不吃青菜,吃不饱饭,每个人的嘴角都裂了,有时候一笑、一大声说话,就渗出血来,大家开玩笑说:“得,不用画口红了。”

过雪山时的徐永亮(上图)和部队进军西藏时过雪山的情景(中、下图)。 (徐永亮供图,8月11日翻拍)
这时徐永亮向我们展示了一张过雪山时的个人照片,画面上的他,有着明显的“高原红”。徐永亮笑着告诉我们:“当时只觉得浑身冒汗,喘不上气来,但带着战士们喊号子,顺利翻过了一个大雪山。后来结婚体检时才知道,那时候我得了结核病。”
文工团后来追随52师由昌都到拉萨,走了一段“最苦的路”,翻了十多座5000米大山,趟的冰河“数都数不过来”,脚下由凉到疼、由疼到麻、由麻到木,直至没有知觉……战士们到达拉萨接受体检时,发现不少女兵已“失去了生育能力”。
一提到当年进藏时所看到的景象,一说起老百姓所受的苦,徐永亮酒难掩愤懑之情:“我真的是见到了什么叫奴隶社会。”
徐永亮说,每逢达赖喇嘛早朝时,那些贵族官员们骑着大马在前,家奴们则一路拼命跑跟随,淹没在尘土飞扬中;那时候,农奴要是见到奴隶主,辫子必须要放下来,舌头要伸出来,说话必须用敬语,否则就会挨鞭子;当时监狱不管饭,犯人带着中间捆着铁棍的脚镣到街头要饭,有的犯人脚被剁了,就在街上爬;不少流浪儿童,没有衣服穿,晚上就和流浪狗睡到了一起……街头处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景象。“我亲眼看到有个妇女死在了街头,一个娃娃还扑在她怀里吃奶呢,后来解放军把这个娃娃救走了。”说到这里,徐永亮攥起了拳头。

农奴制度下流落街头、乞讨求生的妇女儿童。(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徐永亮说,部队刚进藏时战士们所见到的拉萨,真的是“又拉又撒”。布达拉宫前面有一个山,有二三层楼那么高,都是粪便和垃圾堆起来的。后来文工团开荒种地没有肥料,用了一个月把那些粪便和垃圾背到了地里。现在,每每通过新闻节目看到拉萨时,徐永亮总是感慨万千:“这变化多大呀,连公共厕所都现代化了。”
在西藏期间,文工团的主要工作是训练和演出,除此之外,还要开荒、种菜、养猪,冬天还得派人弄土豆和萝卜。演员们走街串巷地表演节目,还要到不同的哨卡去演出,完成150场的演出任务起码需要半年时间。

图为文工团在西藏开荒种菜。(徐永亮供图,8月11日翻拍)
“进军西藏和在西藏的日子,这在当时也没觉得有多苦,现在回想起来,”徐永亮停顿了一下,说,“能把西藏的苦吃下来,以后再遇到什么苦,就觉得不是什么苦事了。”
剪不断的西藏情
“可以说,我把我的青春献给那个地方了,我对那个地方确实有剪不断的情感,尤其是回忆起我们进藏时的那种情怀,真的难以割舍。”徐永亮接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他难忘的老阿妈的故事。
1951年7月,徐永亮所在18军54师文工队进驻甘孜修机场时,需要借助老百姓的房子,他第一次见到了藏族老阿妈。老阿妈脸黑黑,抹的酥油,“光露着两个眼睛”,尽管她在善意地频频招手,还是把时年十几岁的徐永亮吓得“想往回跑”。随着相处,徐永亮日渐感受到了藏族同胞的善意——战士们每天出工回来,老阿妈都会提前把热水烧好,一盆一盆地填满,供大家洗澡、擦身子。
徐永亮叹了口气,说:“我们有的人把终身献给了西藏,有的还把儿女们也献给了西藏。”
像徐永亮这样为西藏奋斗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兵,为了“长期援藏”,他们不少人错过了为人父母最重要的时光。他们的小孩出生以后,有的被送回了老家交给家里人照顾,有的被送到了后方的幼儿园、八一小学。这些孩子往往只知道自己的父母在西藏,但长年没见过面。有些兄妹先后进了同一个学校上学,却彼此不认识。当父母回去接孩子时,孩子会躲起来,只叫他们“叔叔”、“阿姨”。每当这个时候,这些老兵就会落泪。
采访间隙,我们有幸见到了徐永亮的大书柜,里面林林总总摆着不少和西藏有关的图书。徐永亮说,有关西藏的书自己只要看见了就都买了,买了之后都看了。

徐永亮家中书柜里有关西藏的图书(摄于8月11日)。 新华网 黄锐 摄
担任西藏军区话剧团副团长时,他曾想派创作人员到高原上去,用几年的时间体验生活,把藏族整个文化、社会犬牙交错的境况如实体现出来。但由于多种原因,“好多计划都没有完成”。
提到《西藏风云》的编剧工作,徐永亮说自己曾向战友大哭过,“因为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表现这个题材了”。
徐永亮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自己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想写一个有关西藏的剧本,名字叫《雪山上的山茶花》,另一个是是希望收集到一枚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的纪念章。
当我们问及心愿是否达成时,徐永亮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说:“身体不行了,已经写不成了。”说起纪念章,徐永亮飞快回答说“还没有”,随后,他眼前一亮,告诉我们说:“但获赠了一块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纪念币,是一位藏族青年送我的。”当时徐永亮特别感动,回赠了一幅作品,题写的内容是“藏汉亲如一家——曾在西藏工作的一名老兵送”。

一位藏族青年送给徐永亮的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纪念币(摄于8月11日)。 新华网 黄锐 摄
徐永亮说,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非常遗憾至今都没能收集到一枚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章。
离开西藏后,徐永亮一直珍存和追忆着那段“激情燃烧的西藏岁月”,并以此慰藉着自己这抹“无处安放的乡愁”。
- 频道周排行
- 频道T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