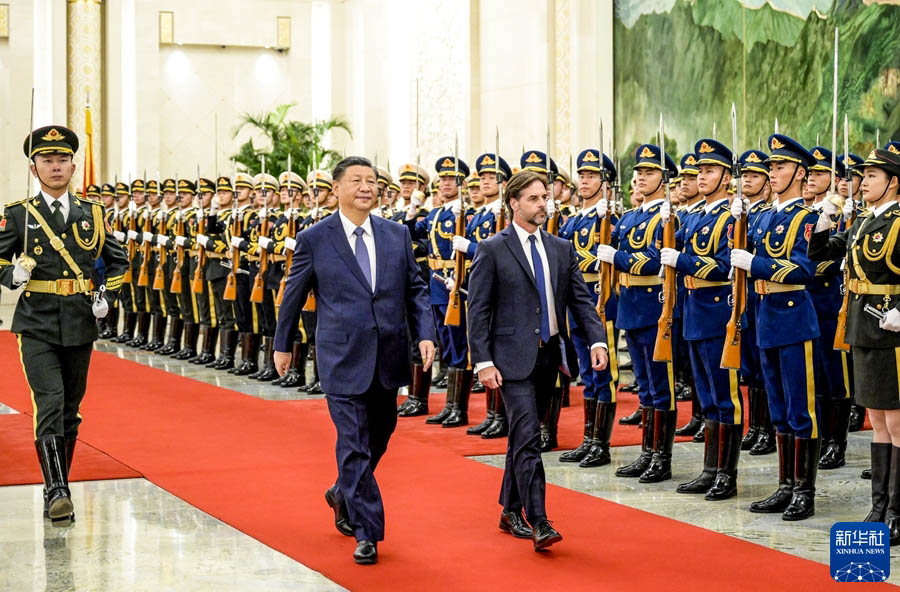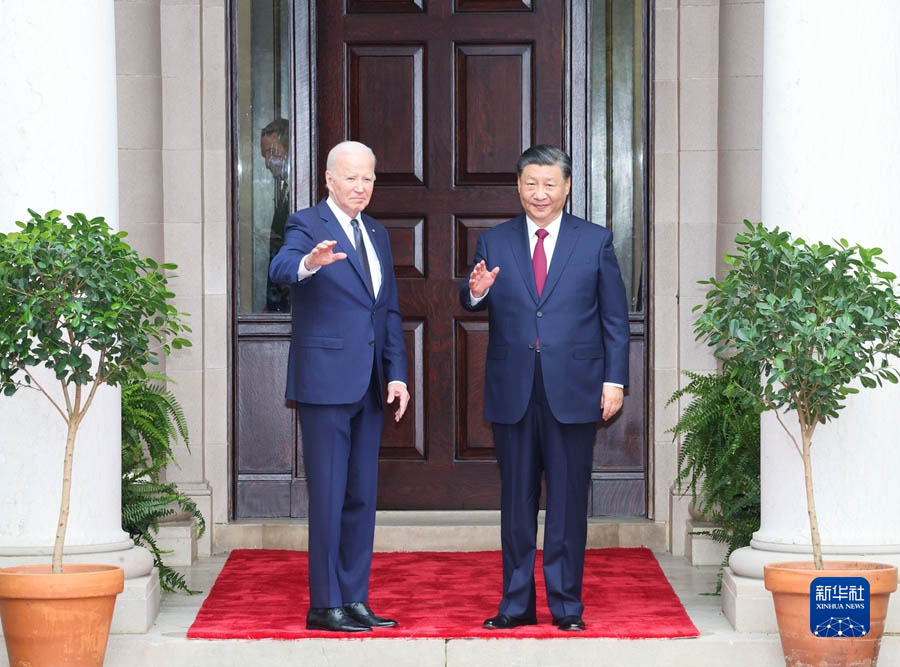入藏三题
2014-03-13 21:11 来源:今日西藏昌都 点击:0
2008年十月下旬,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生平第一次进藏。当火车从西宁站徐徐启动,成年以来,所有关于西藏的种种想象和猜疑也渐次萌动。那种莫名的期待和欣喜,让人难以入睡。
列车奔驰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上。当经过唐古拉山口以后,车厢内开始供氧。尽管如此,高原反应还是如期而至。我感到头痛欲裂,烦躁不安。但是,窗外的风景很快就吸引了乘客们的注意。有人说,西藏是一天四季,因为这里是世界上环境最严酷、气候变化最大的地区之一。在列车上,我们真的目睹了一天中间从艳阳高照到雨雪霏霏的过程。前一张照片拍的还是在草地徜徉的牦牛,后一张里面却是风雪交加的连绵雪山。仿佛是一年四季迅速的在眼前轮换,翻页一样的续写。一如我后面的体悟,在高原上短短的十日,生命也被高度压缩了。
直到一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难忘一个刻骨铭心的画面。当列车穿过可可西里藏羚羊自然保护区以后,我看到了一个在漫天雪花中,叩着长头逆风行进的藏民。苍茫天地间,只有无穷无尽的雪山、荒原,只有无穷无尽的天空和大地,这样一个渺小的身影,却坚定的一点一点向前挺进。也许任何关于这种举动意义的追问,在此时都是愚蠢的。我想起了一位光明日报的老记者说过的话,他说,“在西藏缺氧,但从不缺精神”,此刻,它是如此真实和震撼。在高原上,最接近天空的地方,人与天地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对话,在交流,我想,也许我们真的要相信,生命是一种修行,生命是一种轮回。
一年后的这个日子,恰逢伟大祖国60年大庆,我回味着自己的这段“藏缘”,真觉得要说点什么。 一.敬畏与净化
在风行一时的《玛吉阿米留言薄》这本书里,有这样两段入藏朋友的留言。“第一次来到拉萨,第一次来到布达拉宫,第一次来到八角街,第一次这样身心疲惫。所有的第一次真的让我永生难忘。难忘这里纯净的天空,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神秘的殿堂。在这样的环境,会使你抛开世间一切烦恼,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体。”(《玛吉阿米留言薄》,北京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90页)另外一段这样写道:“此时此刻坐在玛吉阿米酒吧,聆听着浓郁藏域风情的音乐,望着窗外灿烂阳光照耀下不停的围绕着八角街转经的人群,心中涌起无限感慨。这是我第三次进藏,青藏、川藏都已走过,尽管所有的经历都已成为历史,所有的风光都已印在相片和脑海中,但西藏永远是我心中的圣地。真不想走,真的不想走,不愿回深圳。也许下辈子我会成为‘藏人’。”(《玛吉阿米留言薄》,北京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9页)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N次,西藏之旅一定会成为人们铭刻终生的记忆。不管是在青藏铁路,还是在雪域高原,一路走过,有人把它比作朝圣,有人把它当成回归。对我而言,就是回归;是向自然回归,向生命回归,向自我回归,向灵魂深处回归。
拉姆拉措湖位于当雄县。藏语的意思是“天女之魂湖”,海拔4000米,是西藏最具传奇色彩的湖泊。每次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等大活佛的转世线索都是由高僧静观这面湖水,透过卜象得到神示的。当我乘车奔赴拉姆拉措湖的时候,眼睛里看到的,是一座又一座雪山,耳朵里听到的,是一首又一首藏歌。那飞遏入云的曲调,让我心醉神迷。听当地人讲,去这个湖是需要运气的,天气不好的时候,根本没法进去。幸运的是,那天一路上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当我到达湖边,眼前是那么大那么大的一片湛蓝,远处是连绵不断的雪山,让人再一次无法言语。此时此刻,什么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什么是“天人合一”,什么是“藻雪精神”,在这里都是了。我情不自禁的躺倒在湖边的白色沙滩上,大脑不知是兴奋还是缺氧,有种眩晕的感觉。虽然远处游人如织,但我却觉得无比安静。安静的体会着片刻即永恒。
这时有游人让我帮忙拍照,大家彼此素不相识,但是在那里,好像一下子没有任何距离。我拍完他们,他们再热情的拍我。只觉得镜头不够用,内存不够大,画面拍不完。而人与人之间,也是那么亲近。现在回头想想,只有在那样一个天大地大的所在,我们仿佛一下子被抛到天荒地老的前世,生命才被一览无余的裸露着,内心充满了对神山圣湖的敬畏。那种脱胎换骨的净化感,真的令人难忘。在返回拉萨的路上,我对友人说,与高原和圣湖相比,平日里那些欲望和苦恼,简直是太微渺和可笑了。生命在这里变得如此简单,生活在这里变得如此纯朴。 二.宗教与世俗
在法国著名的藏学家石泰安的名作《西藏的文明》这本书里,有这样一段叙述:“这是一个包括无数形态的极端复杂的领域;一种洞察入微和内容丰富的哲学,同时包括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一种非常深奥的心理学,它与冥想静修和控制心理生理学作用(瑜伽)的修持法有着密切联系;不计其数的诸神;不胜枚举的仪轨;民间修持;宇宙形态的思辨和占卜术。对于其中的每一种形态,西藏人都曾编写过成千上万卷论著。”这是对藏传佛教的一个概括。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不仅是人类宗教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篇章。对于门外汉的我,只能怀着一颗虔敬的心,面对群山之巅金碧辉煌的佛殿,面对身披袈裟默默无语的僧人,面对山崖上风中飞舞的经幡,面对手持转经筒虔诚诵经的藏民。
在日常生活中,我看到的最直接的藏传佛教宗教活动似乎只有普通藏胞磕长头了。有人说,藏民一辈子一定要在佛前磕够十万个头,否则是不能转世的。再多的那些,就是给自己积德了。大昭寺前有一堵高墙,高墙下面的开阔地上,铺着一排一排的垫子,不少虔诚的藏民不远千里一路叩拜,来到这里,放下铺盖,日复一日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双脚并立,双手高举,俯身跪拜,匍匐在地。再起身,再跪拜。这就是所谓的磕长头。
站在大昭寺的顶层,俯瞰下去,那些口中念念有词连番跪拜的藏胞,让我们这些外乡人既感动又茫然。我又想起了在青藏铁路沿线看到的那个顶着风雪磕着长头一点一点移动的身影。我不知道在这样一套动作中包含着什么样的意义。但是,我坚信一点,这种十分耗费体力的跪拜,是在用身体的疲惫,换来灵魂的安宁。
大昭寺里珍藏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而且据说是佛祖亲自开光的。但是,这就是藏胞们虔诚叩拜的唯一理由吗?在八角街上,我拍到一张手持转经筒转经的老人,在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和高原一样的淡定、宁静和深邃。也许,越是恶劣的自然条件,人的精神力量就越是强大。越是物质生活贫乏,神的光辉就越发神圣。在这样简单的跪拜中,也许包含着普通藏胞关于前世今生,关于来世生活的全部祈愿。他们跪拜的不仅是佛祖,也是自己。
驱车行进在高原,宗教的力量像是山顶的经幡一样无处不在。在人迹罕至的绝壁,在陡峭如刀的高崖,我们随处可见随风飞舞的经幡,它们仿佛在召唤什么。而山脚下一排一排由政府补贴修建的簇新的藏式民居里,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像酥油茶和菩萨像,和谐有机的摆放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到一位藏胞家中做客,在客厅里最显著的位置上,悬挂着共和国四代领袖的画像,有趣的是,四位领袖人物是在同一张图片上出现的。逐个房间参观时,却发现有个屋子是专门敬佛的。藏胞告诉我们,他们既相信共产党,也相信达赖和班禅。追问理由,藏胞的回答是,共产党带给我们富裕的生活,达赖和班禅是我们的精神导师。我想,这是智慧的藏胞,智慧的回答,也是藏文化包容性的一个生动体现。
但是,年轻的藏胞还会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对于宗教那么虔诚吗?入夜,漫步在拉萨街头,随便走进一家藏式酒吧,总是有音乐和啤酒的。在一家据说是十分有名的藏式酒吧,我和朋友一起听到了纯正的藏语摇滚。舞台上,两个帅气的年轻藏族小伙子,衣着时尚,发型前卫。他们用发自肺腑的嘶吼,打破了高原夜空的寂静。舞台下面坐满了一边喝酒,一边谈笑风生的藏族男女青年,我只在他们颈子上、手腕上缠绕的藏银饰品上,寻觅到一点点佛的印记。
三.传统与现代
2009年,一部由旅英华人独立拍摄制作的纪录片《西藏一年》,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西藏一年》以西藏第三大城镇、农牧业占80%的江孜为拍摄地点。摄制组在那里生活了一年,以田野考察的人类学方式,跟拍了8位普通藏族人一年四季的生活、劳动,包括诵经、婚恋、庆生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都出生在江孜农村,分别是:妇女干部、乡村医生、饭店经理、三轮车夫、冰雹喇嘛和包工头。
2008年3月6日,《西藏一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首播,随后《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星期日独立报》、《金融时报》、《每日邮报》等英国各媒体都对该片进行了报道。此后,《西藏一年》又被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挪威、阿根廷、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南非、韩国以及覆盖整个非洲的非洲电视广播联合体、覆盖整个拉美的拉美电视广播联合体、覆盖整个亚洲的发现频道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电视台订购与播放。英国广播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已经连续三次播放《西藏一年》。中央电视台也于2009年7月27日播出该片。
英国《卫报》评价该片说,“以罕见的深度、惊心动魄的力量,公正记录当今最有争议、最偏远地方人们的真实生活。”该片播出后,就连达赖喇嘛也设法联系该片导演书云,对《西藏一年》表示认同。这是2008年拉萨3.14事件以后,享誉世界的一部华人导演的重要纪录片作品。而其中,让我引起深刻共鸣的,是影片中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名叫拉巴的三轮车夫在江孜长达半年的漫长冬天里,每天站在街头等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一上午六小时没有一个客人,江孜冬天的风很大,一过下午三点可以达到八级,这么大的风根本就没有人坐车,拉巴也没有办法,家里就揭不开锅,他只好去掏厕所,把那个厕所一年攒的粪全部都掏出来。
拉巴在父亲去世那年辍学了,他只读到了高一。没有文凭,没有手艺,他很难找到一份工作。但他有一个好身体,从拉三轮、卸货、掏厕所到贩狗,只要能挣钱,只要不违法,他什么苦都能吃。拉巴非常喜欢的侄子欧珠有先天性心脏病,寒冷的冬天使侄子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被送进江孜县医院紧急抢救。侄子被抢救过来了。藏历新年大年初一,拉巴咬牙为侄子买了鞭炮和礼花,全家高高兴兴过新年。但要彻底解决侄子的心脏病需要18万元手术费,否则,侄子只能活到十几岁。这对拉巴一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拉巴不想放弃,他说他一定要挣钱,给自己的侄子治病。
据导演介绍说,在这样一个故事里,还隐含着一个更深刻的背景。2000年之后,很多从甘肃、四川打工来的汉族人,把一些不需要太多技术的活儿慢慢给干起来了。拉巴没有上过学,而且没有手艺。拉巴想做出租车司机,他哥哥是交通局局长,但单位很喜欢用内地的出租车司机,因为内地司机不喝酒,而且有很多驾驶经验。应该说,这是去年3.14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藏族年轻人都面临的困惑。
有人评价说,美国200年完成的事情,在中国只用了30年。而西藏社会在最近十年,更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通讯、交通、居住条件的改善;旅游、医药、养殖等各种产业的发展;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来自全国各地或者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讯息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一切的一切,使传统的西藏社会不可避免的承受着被撕扯、被改变的压力。那些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小人物,又成为这种压力最直接的承载者。藏胞拉巴的遭遇和故事,在汉族社会也同样上演着。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落差,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如果它与民族问题不期而遇,便会激发出让我们始料未及的冲突和矛盾,这也似乎成为当下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在入藏短短的十天中,我切身感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坚守与现代的喧嚣的碰撞。发展和保护,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也许,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置身高原,应该还原到常识和人性,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心理等多种手段,用尊重化解对抗,用仁慈消融隔阂。正如《西藏一年》的导演书云所说,“对西藏普通的百姓而言,他们需要对过去灿烂历史文化的记忆,但更需要在变化中追求现代化的美好未来。他们渴望享受现代化的生活,不希望被当作古老的文物加以收藏和展示,更不希望把他们当作虚拟中的‘香格里拉’或‘香巴拉’让人观摩,被人误解、误会。”
总之,入藏十日,回味终生。我想,西藏不仅对于那些全然无知的外国朋友,同样对于知之甚少的中国民众,都具有重新探访,重新发现的深刻意义。
附:郑世明简历
郑世明,1970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祖籍孟津。本科及研究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1995年至2000年就职于河南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从事记者、编导工作。2000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获电影学博士学位。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中选“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的“国际交流学者”项目,赴韩国中央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艺术学会会员,北京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在《现代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河南大学学报》、《电视研究》等权威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代表性的论文包括《文化命名权的搬演——透视央视大赛策略》,《论电视媒介权力的概念及内涵》、《在权力视野中对电视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义》、《消费语境下电视游戏娱乐节目探微》等。2006年元月出版专著《权力的影像——权力视野中的中国电视媒介研究》。
- 频道周排行
- 频道TOP10